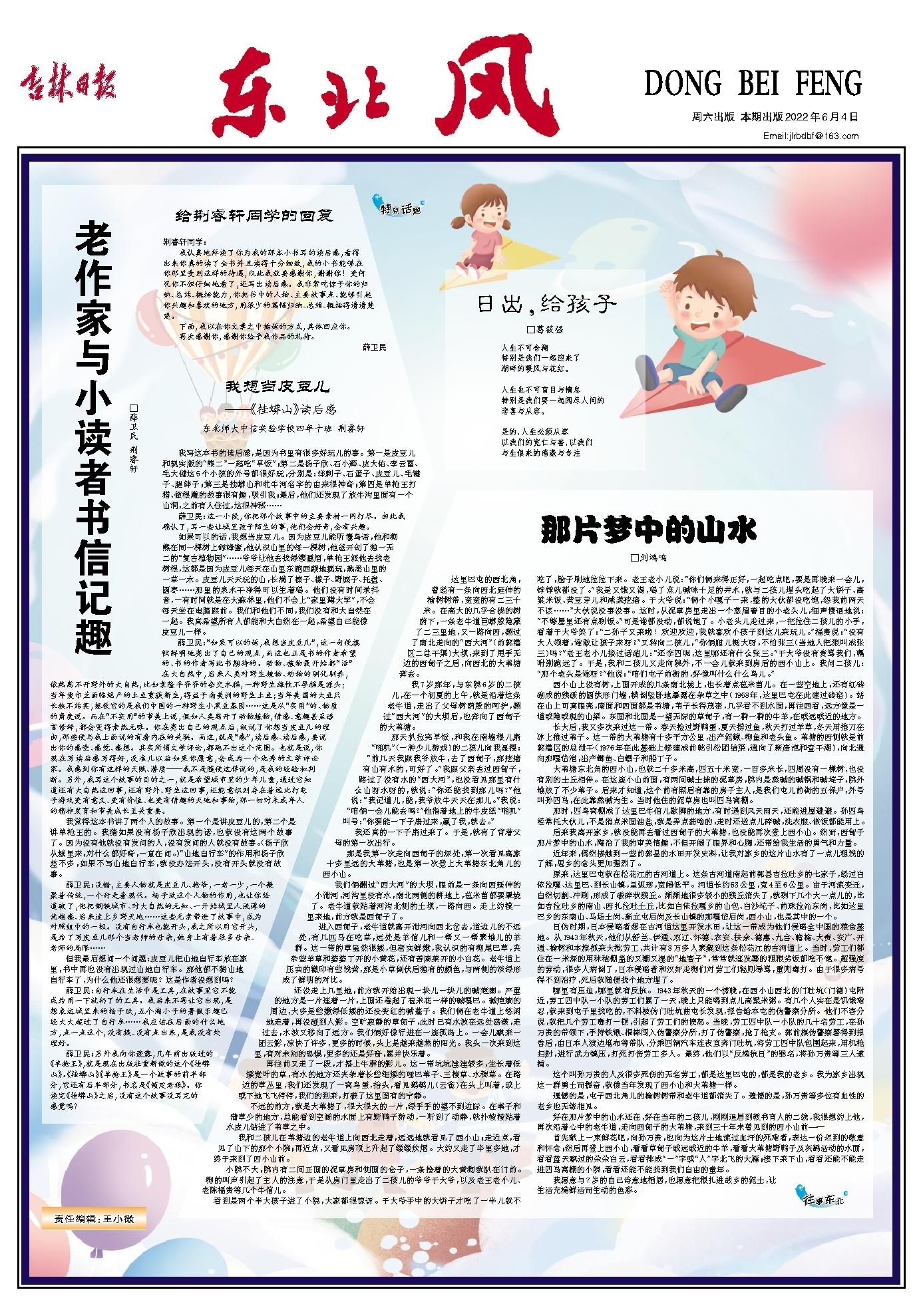达里巴屯的西北角,曾经有一条向西北延伸的榆树树带,宽宽的有二三十米。在高大的几乎合拢的树荫下,一条老牛道巨蟒般隐藏了二三里地,又一路向西,翻过了南北走向的“西大河”(前郭灌区二总干渠)大坝,来到了甩手无边的西甸子之后,向西北的大苇塘奔去。
我7岁那年,与东院6岁的二孩儿,在一个初夏的上午,就是沿着这条老牛道,走出了父母树荫般的呵护,翻过“西大河”的大坝后,也奔向了西甸子的大苇塘。
那天扒拉完早饭,和我在南墙根儿扇“啪叽”(一种少儿游戏)的二孩儿向我显摆:“前几天我跟我爷放牛,去了西甸子,那疙瘩有山有水的,可好了。”我跟父亲去过西甸子,路过了没有水的“西大河”,也没看见那里有什么山呀水呀的,就说:“你还能找到那儿吗?”他说:“我记道儿,能,我爷放牛天天在那儿。”我说:“咱俩一会儿能去吗?”他指着地上的牛皮纸“啪叽”叫号:“你要能一下子扇过来,赢了我,就去。”
我还真的一下子扇过来了。于是,就有了背着父母的第一次出行。
那是我第一次走向西甸子的深处,第一次看见离家十多里远的大苇塘,也是第一次登上大苇塘东北角儿的西小山。
我们俩翻过“西大河”的大坝,眼前是一条向西延伸的小泄河,河沟里没有水,南北两侧的耕地上,苞米苗都要罩垅了。老牛道就贴着河沟北侧的土坝,一路向西。走上约摸一里来地,前方就是西甸子了。
进入西甸子,老牛道就离开泄河向西北岔去,道边儿的不远处,有几匹马在吃草,远处是羊倌儿和一帮又一帮聚堆儿的羊群。这一带的草虽然很矮,但密实鲜嫩,我认识的有狗尾巴草,夹杂些羊草和婆婆丁开的小黄花,还有苦麻菜开的小白花。老牛道上压实的辙印有些浅黄,那是小草倒伏后独有的颜色,与两侧的淡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没走上几里地,前方就开始出现一块儿一块儿的碱疤瘌。严重的地方是一片连着一片,上面还卷起了苞米花一样的碱嘎巴。碱疤瘌的周边,大多是些嫩绿低矮的还没变红的碱蓬子。我们俩在老牛道上悠闲地走着,再没碰到人影。空旷寂静的草甸子,此时已有水波在远处荡漾,走过去,水波又移向了远方。我们俩好像行进在一座孤岛上。一会儿飘来一团云影,凉快了许多,更多的时候,头上是越来越热的阳光。我头一次来到这里,有对未知的恐惧,更多的还是好奇,累并快乐着。
再往前又走了一段,才搭上牛群的影儿。这一带坑坑洼洼较多,生长着低矮宽叶的草,有水的地方还夹杂着长些细矮的哑巴苇子、三棱草、水稗草。在路边的草丛里,我们还发现了一窝鸟蛋,抬头,看见鹅鹌儿(云雀)在头上叫着,或上或下地飞飞停停,我们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固有的宁静。
不远的前方,就是大苇塘了,很大很大的一片,绿乎乎的望不到边际。在苇子和蒲草少的地方,总能看到空阔的水面上有野鸭子游动,一听到了动静,就扑棱棱贴着水皮儿钻进了苇草之中。
我和二孩儿在苇塘边的老牛道上向西北走着,远远地就看见了西小山;走近点,看见了山下的那个小院;再近点,又看见房顶上升起了缕缕炊烟。大约又走了半里多地,才终于来到了西小山前。
小院不大,院内有二间正面的泥草房和侧面的仓子,一条拴着的大黄狗就趴在门前。狗的叫声引起了主人的注意,于是从房门里走出了二孩儿的爷爷于大爷,以及老王老小儿、老陈福贵等几个牛倌儿。
看到是两个半大孩子进了小院,大家都很惊讶。于大爷手中的大饼子才吃了一半儿就不吃了,脸子刷地拉拉下来。老王老小儿说:“你们俩来得正好,一起吃点吧,要是再晚来一会儿,饽饽就都没了。”我是又饿又渴,喝了点儿碱味十足的井水,就与二孩儿埋头吃起了大饼子、高粱米饭、黄豆芽儿和咸菜疙瘩。于大爷说:“俩个小嘎子一来,整的大伙都没吃饱,怨我前两天不该……”大伙说没事没事。这时,从泥草房里走出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儿,细声慢语地说:“不够屋里还有点剩饭。”可是谁都没动,都说饱了。小老头儿走过来,一把拉住二孩儿的小手,看着于大爷笑了:“二孙子又来啦!欢迎欢迎,我就喜欢小孩子到这儿来玩儿。”福贵说:“没有大人领着,谁敢让孩子来呀?”又转向二孩儿,“你俩胆儿挺大呀,不怕张三(当地人把狼叫成张三)吗?”老王老小儿接过话碴儿:“还李四呢,这里哪还有什么张三。”于大爷没有责骂我们,嘱咐别跑远了。于是,我和二孩儿又走向院外,不一会儿就来到房后的西小山上。我问二孩儿:“那个老头是谁呀?”他说:“咱们屯子前街的,好像叫什么什么鸟儿。”
西小山上没有树,上面开成的几条南北垅上,也长着点苞米苗儿。在一些空地上,还有红砖砌成的残破的圆拱形门墙,横倒竖卧地暴露在杂草之中(1958年,达里巴屯在此建过砖窑)。站在山上可真眼亮,南面和西面都是苇塘,苇子长得茂密,几乎看不到水面,再往西看,远方像是一道或隐或现的山梁。东面和北面是一望无际的草甸子,有一群一群的牛羊,在或远或近的地方。
长大后,我又多次来过这一带。春天捡过野鸭蛋,夏天捞过鱼,秋天打过羊草,冬天用推刀在冰上推过苇子。这一带的大苇塘有十多平方公里,出产泥鳅、狗鱼和老头鱼。苇塘的西侧就是前郭灌区的总泄干(1976年在此基础上修建成前乾引松团结渠,通向了新庙泡和查干湖),向北通向那嘎岱泡,出产鲫鱼、白鳔子和船丁子。
大苇塘东北角的西小山,也就二十多米高,四五十米宽,一百多米长,四周没有一棵树,也没有别的土丘相伴。在这座小山前面,有两间碱土抹的泥草房,院内是熬碱的碱锅和碱垞子,院外堆放了不少苇子。后来才知道,这个前有照后有靠的房子主人,是我们屯儿前街的五保户,外号叫孙四鸟,在此靠熬碱为生。当时他住的泥草房也叫四鸟窝棚。
那时,四鸟窝棚成了达里巴牛倌儿歇脚的地方,有时遇到风天雨天,还能进屋避避。孙四鸟经常托大伙儿,不是捎点米面油盐,就是弄点药啥的,走时还送点儿碎碱,洗衣服、做饭都能用上。
后来我离开家乡,就没能再去看过西甸子的大苇塘,也没能再次登上西小山。然而,西甸子那片梦中的山水,陶冶了我的审美情趣,不但开阔了眼界和心胸,还带给我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近年来,偶然接触到一些前郭县的水田开发史料,让我对家乡的这片山水有了一点儿粗浅的了解,思乡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原来,达里巴屯就在松花江的古河道上。这条古河道南起前郭县吉拉吐乡的七家子,经过白依拉嘎、达里巴、到长山镇,呈弧形,宽阔低平。河道长约58公里,宽4至6公里。由于河流变迁,自然切割、冲刷,形成了破碎状残丘。渐渐地很多较小的残丘消失了,就剩下几个大一点儿的,比如吉拉吐乡的南山、西扎拉吐土丘,比如白依拉嘎乡的山包、白沙坨子、前珠拉沁东岗,比如达里巴乡的东南山、马场土岗、新立屯后岗及长山镇的那嘎岱后岗,西小山,也是其中的一个。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想在古河道这里开发水田,让这一带成为他们侵略全中国的粮食基地。从1943年秋天,他们从舒兰、伊通、双辽、怀德、农安、扶余、德惠、九台、瞻榆、大赉、安广、开通、榆树和本旗抓来大批劳工,共计有8万多人聚集到这条松花江的古河道上。当时,劳工们都住在一米深的用秫秸棚盖的又潮又湿的“地窨子”,常常就连发霉的粗粮劣饭都吃不饱。超强度的劳动,很多人病倒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对劳工们轻则辱骂,重则毒打。由于很多病号得不到治疗,死后就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西小山西北的门吐坑(门德)屯附近,劳工四中队一小队的劳工们累了一天,晚上只能喝到点儿高粱米粥。有几个人实在是饥饿难忍,就来到屯子里找吃的,不料被伪门吐坑曲屯长发现,报告给本屯的伪警察分所。他们不容分说,就把几个劳工毒打一顿,引起了劳工们的愤怒。当晚,劳工四中队一小队的几十名劳工,在孙万贵的带领下,手持铁锹、棍棒闯入伪警察分所,打了伪警察,抢了枪支。郭前旗伪警察署得到报告后,由日本人渡边堪布等带队,分乘四辆汽车连夜直奔门吐坑,将劳工四中队包围起来,用机枪扫射,进行武力镇压,打死打伤劳工多人。最终,他们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将孙万贵等三人逮捕。
这个叫孙万贵的人及很多死伤的无名劳工,都是达里巴屯的,都是我的老乡。我为家乡出现这一群勇士而振奋,就像当年发现了西小山和大苇塘一样。
遗憾的是,屯子西北角儿的榆树树带和老牛道都消失了。遗憾的是,孙万贵等多位有血性的老乡也无缘相见。
好在那片梦中的山水还在,好在当年的二孩儿,刚刚退居到教书育人的二线,我很想约上他,再次沿着心中的老牛道,走向西甸子的大苇塘,来到三十年未曾见到的西小山前——
首先献上一束鲜花吧,向孙万贵,也向为这片土地流过血汗的死难者,表达一份迟到的敬意和怀念;然后再登上西小山,看看草甸子或远或近的牛羊,看看大苇塘野鸭子及灰鹤活动的水面,看看蓝天飘过的朵朵白云,看看排成“一”字或“人”字北飞的大雁;接下来下山,看看还能不能走进四鸟窝棚的小院,看看还能不能找到我们自由的童年。
我愿意与7岁的自已诗意地栖居,也愿意把根扎进故乡的泥土,让生活充满鲜活而生动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