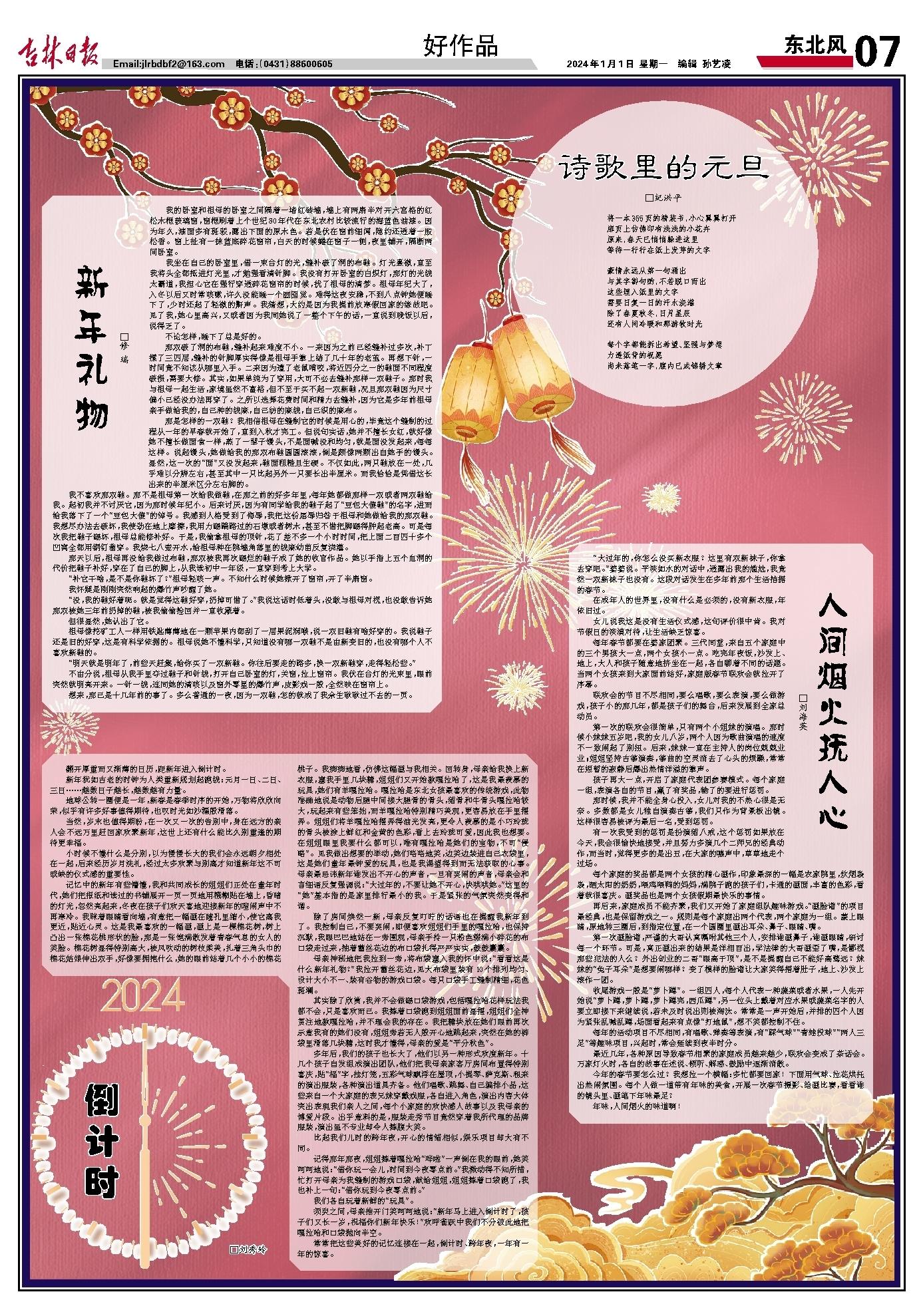我的卧室和祖母的卧室之间隔着一堵红砖墙,墙上有两扇半对开六宫格的红松木框玻璃窗,窗框刷着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东北农村比较流行的海蓝色油漆。因为年久,漆面多有斑驳,露出下面的原木色。若是伏在窗前细闻,隐约还透着一股松香。窗上扯有一抹蓝底碎花窗帘,白天的时候蜷在窗子一侧,夜里铺开,隔断两间卧室。
我坐在自己的卧室里,借一束台灯的光,缝补破了洞的布鞋。灯光熹微,直至我将头全部抵进灯光里,才勉强看清针脚。我没有打开卧室的白炽灯,那灯的光线太霸道,我担心它在强行穿透碎花窗帘的时候,扰了祖母的清梦。祖母年纪大了,入冬以后又时常咳嗽,许久没能睡一个囫囵觉。难得这夜安稳,不到八点钟她便睡下了,少时还起了轻微的鼾声。我猜想,大约是因为我提前放寒假回家的缘故吧。见了我,她心里高兴,又或者因为我同她说了一整个下午的话,一直说到晚饭以后,说得乏了。
不论怎样,睡下了总是好的。
那双破了洞的布鞋,缝补起来难度不小。一来因为之前已经缝补过多次,补丁摞了三四层,缝补的针脚厚实得像是祖母手掌上结了几十年的老茧。再想下针,一时间竟不知该从哪里入手。二来因为遭了老鼠啃咬,将近四分之一的鞋面不同程度破损,需要大修。其实,如果单纯为了穿用,大可不必去缝补那样一双鞋子。那时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家境虽然不富裕,但不至于买不起一双新鞋,况且那双鞋因为尺寸偏小已经没办法再穿了。之所以选择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缝补,因为它是多年前祖母亲手做给我的,自己种的线麻,自己纺的麻线,自己织的麻布。
那是怎样的一双鞋?我相信祖母在缝制它的时候是用心的,毕竟这个缝制的过程从一年的早春就开始了,直到入秋才完工。但说句实话,她并不擅长女红,就好像她不擅长做面食一样,蒸了一辈子馒头,不是面碱没和均匀,就是面没发起来,每每这样。说起馒头,她做给我的那双布鞋圆圆滚滚,倒是颇像两颗出自她手的馒头。显然,这一次的“面”又没发起来,鞋面粗糙且生硬。不仅如此,两只鞋放在一处,几乎难以分辨左右,甚至其中一只比起另外一只要长出半厘米。而我恰恰是凭借这长出来的半厘米区分左右脚的。
我不喜欢那双鞋。那不是祖母第一次给我做鞋,在那之前的好多年里,每年她都做那样一双或者两双鞋给我。起初我并不讨厌它,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后来讨厌,因为有同学给我的鞋子起了“豆包大傻鞋”的名字,进而给我落下了一个“豆包大傻”的绰号。我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我把这份屈辱归咎于祖母和她做给我的那双鞋。我想尽办法去破坏,我使劲在地上摩擦,我用力踢踹路过的石墩或者树木,甚至不惜把脚踢得肿起老高。可是每次我把鞋子踢坏,祖母总能修补好。于是,我偷拿祖母的顶针,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时间,把上面二百四十多个凹窝全部用钢钉凿穿。我烧七八壶开水,给祖母种在院墙角落里的线麻幼苗反复浇灌。
那天以后,祖母再没给我做过布鞋,那双被我再次踢烂的鞋子成了她的收官作品。她以手指上五个血洞的代价把鞋子补好,穿在了自己的脚上,从我读初中一年级,一直穿到考上大学。
“补它干啥,是不是你鞋坏了?”祖母轻咳一声。不知什么时候她掀开了窗帘,开了半扇窗。
我怀疑是刚刚突然响起的爆竹声吵醒了她。
“没,我的鞋好着呢。就是觉得这鞋好穿,扔掉可惜了。”我说这话时低着头,没敢与祖母对视,也没敢告诉她那双被她三年前扔掉的鞋,被我偷偷捡回并一直收藏着。
但很显然,她认出了它。
祖母像挖矿工人一样用铁匙薄薄地在一颗苹果内部刮了一层果泥润喉,说一双旧鞋有啥好穿的。我说鞋子还是旧的好穿,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祖母说她不懂科学,只知道没有哪一双鞋不是由新变旧的,也没有哪个人不喜欢新鞋的。
“明天就是明年了,前些天赶集,给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往后要走的路多,换一双新鞋穿,走得轻松些。”
不由分说,祖母从我手里夺过鞋子和针线,打开自己卧室的灯,关窗,拉上窗帘。我伏在台灯的光束里,眼前突然就明亮开来。一针一线,连同她的清咳以及窗外零星的爆竹声,皮影戏一般,全然映在窗帘上。
想来,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多么普通的一夜,因为一双鞋,怎的就成了我余生耿耿过不去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