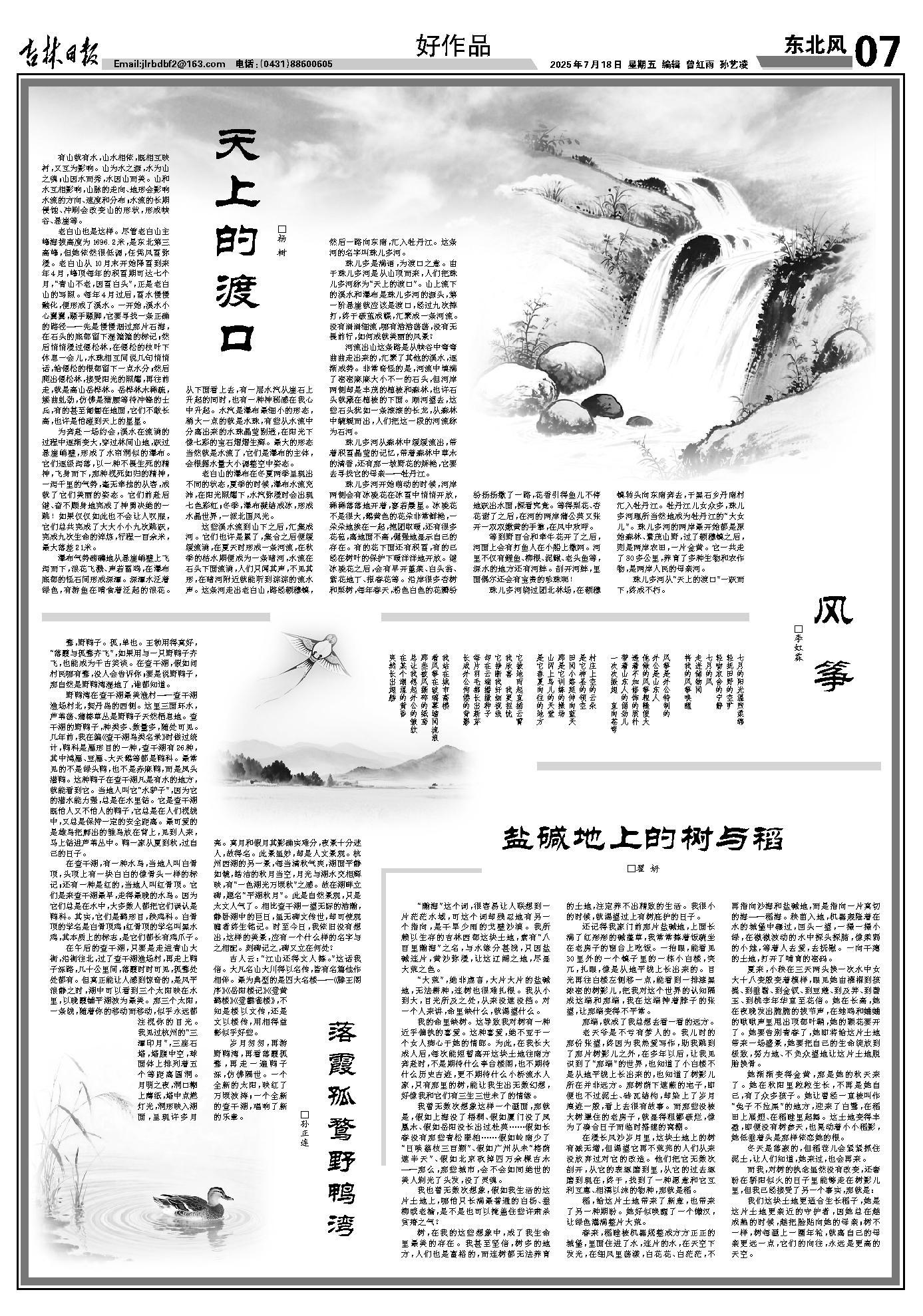“瀚海”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片茫茫水域,可这个词却残忍地有另一个指向,是干旱少雨的戈壁沙漠。我所赖以生存的吉林西部这块土地,素有“八百里瀚海”之名,与水缘分甚浅,只因盐碱连片,黄沙弥漫,让这辽阔之地,尽显大荒之色。
“大荒”,绝非虚言,大片大片的盐碱地,无法耕种,连树也很难扎根。我从小到大,目光所及之处,从来没遮没挡。对一个人来讲,命里缺什么,就渴望什么。
我的命里缺树。这导致我对树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这种喜爱,绝不亚于一个女人痴心于她的情郎。为此,在我长大成人后,每次能短暂离开这块土地往南方奔赴时,不是期待什么亭台楼阁,也不期待什么历史古迹,更不期待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只有那里的树,能让我生出无数幻想,好像我和它们有三生三世未了的情缘。
我曾无数次想象这样一个画面,那就是,假如上海没了梧桐、假如厦门没了凤凰木、假如岳阳没长出过杜英……假如长春没有那些青松翠柏……假如岭南少了“日啖荔枝三百颗”、假如广州从未“榕荫遮半天”、假如北京砍掉四万余棵古木——那么,那些城市,会不会如同绝世的美人剃光了头发,没了灵魂。
我也曾无数次想象,假如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哪怕只长满最普通的白杨、垂柳或老榆,是不是也可以掩盖住些许肃杀贫瘠之气?
树,在我的这些想象中,成了我生命里最美的存在。我甚至坚信,树多的地方,人们也是富裕的,而连树都无法养育的土地,注定养不出精致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就渴望过上有树庇护的日子。
还记得我家门前那片盐碱地,上面长满了红彤彤的碱蓬草,我常常捧着饭碗坐在老房子的窗台上吃饭。一抬眼,能看见30里外的一个镇子里的一栋小白楼,突兀,扎眼,像是从地平线上长出来的。目光再往白楼左侧移一点,能看到一排漆黑浓密的树影儿,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隔成这端和那端,我在这端抻着脖子的张望,让那端变得不平常。
那端,就成了我总想去看一看的远方。
老天爷是不亏有梦人的。我儿时的那份张望,终因为我热爱写作,助我跳到了那片树影儿之外,在多年以后,让我见识到了“那端”的世界,也知道了小白楼不是从地平线上长出来的,也知道了树影儿所在并非远方。那树荫下遮蔽的宅子,即便也不过泥土、砖瓦结构,却染上了岁月痕迹一般,看上去很有故事。而那些没被大树罩住的老房子,就显得粗鄙破烂,像为了凑合日子而临时搭建的窝棚。
在漫长风沙岁月里,这块土地上的树有减无增,但渴望它再不荒芜的人们从来没放弃过对它的改造。他们把它无数次剖开,从它的表琢磨到里,从它的过去琢磨到现在,终于,找到了一种愿意和它互利互惠、相濡以沫的物种,那就是稻。
稻,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新意,也带来了另一种期盼。她好似唤醒了一个懒汉,让绿色灌满整片大荒。
春来,稻畦被机器规整成方方正正的城堡,里面住进了水,连片的水,在天空下发光,在细风里荡漾,白花花、白茫茫,不再指向沙海和盐碱地,而是指向一片真切的海——稻海。秧苗入地,机器轰隆着在水的城堡中碾过,回头一望,一撮一撮小绿,在微微波动的水中探头探脑,像柔弱的小娃,等着人去爱,去抚慰。一向干瘪的土地,打开了哺育的密码。
夏来,小秧在三天两头换一次水中女大十八变般变着模样,眼见她由襁褓到孩提、到垂髫、到金钗、到豆蔻、到及笄、到碧玉、到桃李年华直至花信。她在长高,她在夜晚发出脆脆的拔节声,在蛙鸣和蛐蛐的啾啾声里甩出顶部叶鞘,她的颖花要开了。她要告别青春了,她即将给这片土地带来一场盛景,她要把自己的生命绽放到极致,努力地、不负众望地让这片土地脱胎换骨。
她渐渐变得金黄,那是她的秋天来了。她在秋阳里粒粒生长,不再是她自己,有了众多孩子。她让曾经一直被叫作“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迎来了白鹭,在稻田上展翅、在稻畦里起舞。这土地变得丰盈,即便没有树参天,也晃动着小小稻影,她低垂着头是那样依恋她的根。
冬天是落寂的,但稻茬儿会紧紧抓住泥土,让人们知道,她来过,也会再来。
而我,对树的执念虽然没有改变,还奢盼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能够走在树影儿里,但我已经接受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
我们这块土地更适合生长稻子,她是这片土地更亲近的守护者,因她总在越成熟的时候,越把脸贴向她的母亲;树不一样,树每画上一圈年轮,就离自己的母亲更远一点,它们的向往,永远是更高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