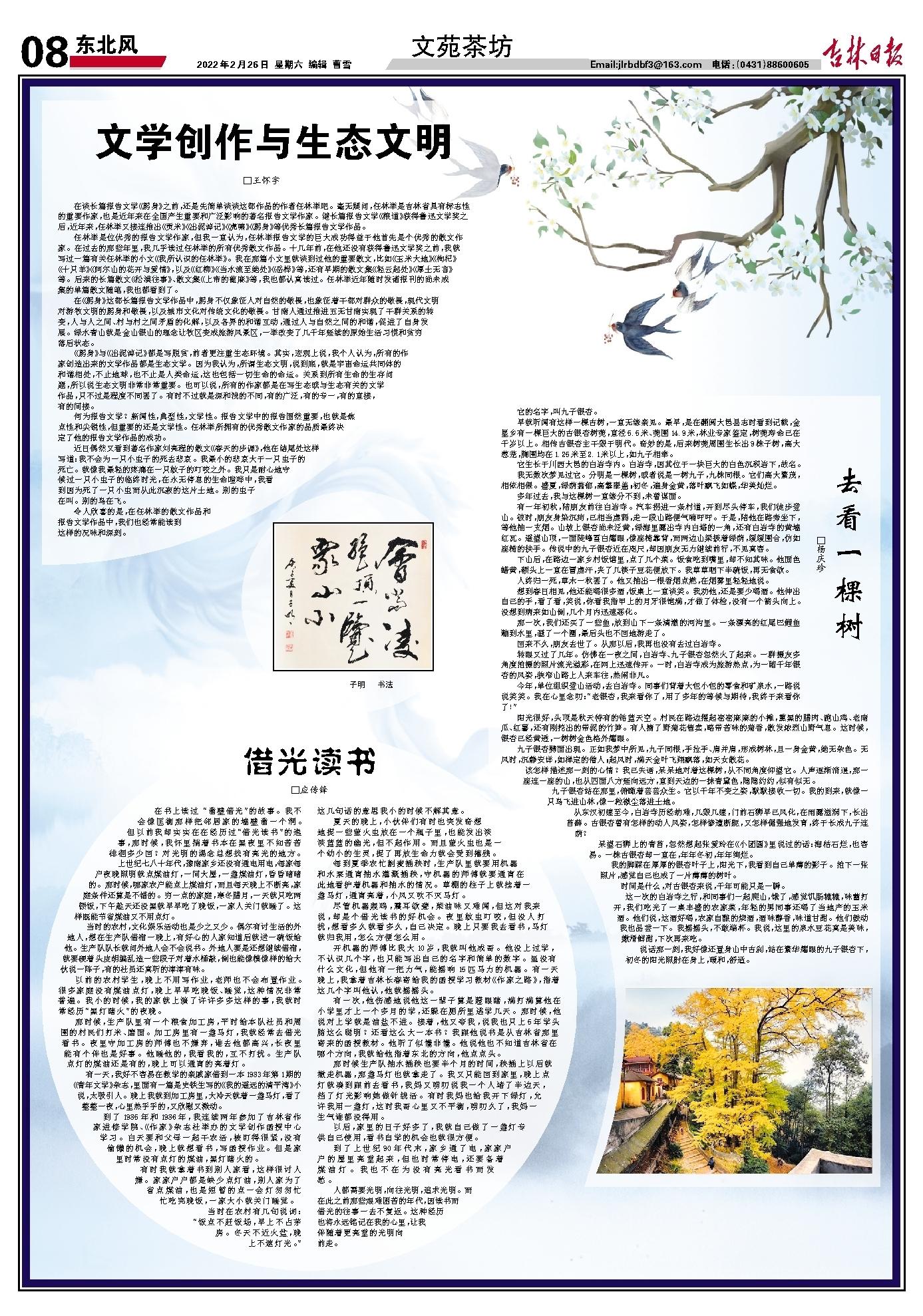在书上读过 “凿壁借光”的故事。我不会像匡衡那样把邻居家的墙壁凿一个洞。但以前我却实实在在经历过“借光读书”的逸事,那时候,我怀里揣着书本在黑夜里不知苦苦徘徊多少回?对光明的渴念总想找有亮光的地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豫南家乡还没有通电用电,每家每户夜晚照明就点煤油灯,一间大屋,一盏煤油灯,昏昏暗暗的。那时候,哪家农户能点上煤油灯,而且每天晚上不断亮,家庭条件还算是不错的。穷一点的家庭,寒冬腊月,一天就只吃两顿饭,下午趁天还没黑就早早吃了晚饭,一家人关门就睡了。这样既能节省煤油又不用点灯。
当时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也是少之又少。偶尔有讨生活的外地人,想在生产队借宿一晚上,有好心的人家知道后就送一碗饭给他。生产队队长就问外地人会不会说书。外地人要是还想继续借宿,就要硬着头皮胡编乱造一些段子对着水桶敲,倒也能像模像样的给大伙说一阵子,有的社员还真听的津津有味。
以前的农村学生,晚上不用写作业,老师也不会布置作业。很多家庭没有煤油点灯,晚上早早吃晚饭、睡觉,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就上演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我就时常经历“黑灯瞎火”的夜晚。
那时候,生产队里有一个粮食加工房,平时给本队社员和周围的村民们打米、磨面。加工房里有一盏马灯,我就经常去借光看书。夜里守加工房的师傅也不嫌弃,谁去他都高兴,长夜里能有个伴也是好事。他睡他的,我看我的,互不打扰。生产队点灯的煤油还是有的,晚上可以通宵的亮着灯。
有一天,我好不容易在教学的亲戚家借到一本1983年第1期的《青年文学》杂志,里面有一篇是史铁生写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太吸引人。晚上我就到加工房里,大冷天就着一盏马灯,看了整整一夜,心里热乎乎的,又欣慰又激动。
到了1985年和1986年,我连续两年参加了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作家》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中心学习。白天要和父母一起干农活,被盯得很紧,没有偷懒的机会,晚上就想看书,写函授作业。但是家里时常没有点灯的煤油,黑灯瞎火的。
有时我就拿着书到别人家看,这样很讨人嫌。家家户户都是缺少点灯油,别人家为了省点煤油,也是短暂的点一会灯匆匆忙忙吃完晚饭,一家大小就关门睡觉。
当时在农村有几句说词:“饭点不赶饭场,早上不占茅房。冬天不近火盆,晚上不遮灯光。”这几句话的意思我小的时候不解其意。
夏天的晚上,小伙伴们有时也突发奇想地捉一些萤火虫放在一个瓶子里,也能发出淡淡蓝蓝的幽光,但不起作用。而且萤火虫也是一个幼小的生灵,捉了再放生命力就会受到摧残。
每到夏季农忙割麦插秧时,生产队里就要用机器和水泵通宵抽水灌溉插秧,守机器的师傅就要通宵在此地看护着机器和抽水的情况。草棚的柱子上就挂着一盏马灯,通宵亮着,小风又吹不灭马灯。
尽管机器轰鸣,震耳欲聋,柴油味又难闻,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个借光读书的好机会。夜里蚊虫叮咬,但没人打扰,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自己决定。晚上只要我去看书,马灯就归我用,怎么方便怎么用。
开机器的师傅比我大10岁,我就叫他成哥。他没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也只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数字。虽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有一把力气,能摇响15匹马力的机器。有一天晚上,我拿着吉林长春寄给我的函授学习教材《作家之路》,指着这几个字叫他认,他就摇摇头。
有一次,他伤感地说他这一辈子算是瞪眼瞎,满打满算他在小学里才上一个多月的学,还躲在厕所里逃学几天。那时候,他说对上学就是油盐不进。接着,他又夸我,说我也只上5年学头脑这么聪明?还看这么大一本书?我跟他说书是从吉林省那里寄来的函授教材。他听了似懂非懂。他说他也不知道吉林省在哪个方向,我就给他指着东北的方向,他点点头。
那时候生产队抽水插秧也要半个月的时间,秧插上以后就撤走机器,那盏马灯也就拿走了。我又只能回到家里,晚上点灯就凑到跟前去看书,我妈又唠叨说我一个人堵了半边天,挡了灯光影响她做针线活。有时我妈也给我开下绿灯,允许我用一盏灯,这时我哥心里又不平衡,唠叨久了,我妈一生气谁都没得用。
以后,家里的日子好多了,我就自己做了一盏灯专供自己使用,看书自学的机会也就很方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家乡通了电,家家户户的屋里亮堂起来,但也时常停电,还要备着煤油灯。我也不在为没有亮光看书而发愁。
人都需要光明,向往光明,追求光明。而在此之前那些艰难困苦的年代,因读书而借光的往事一去不复返。这种经历也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让我伴随着更亮堂的光明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