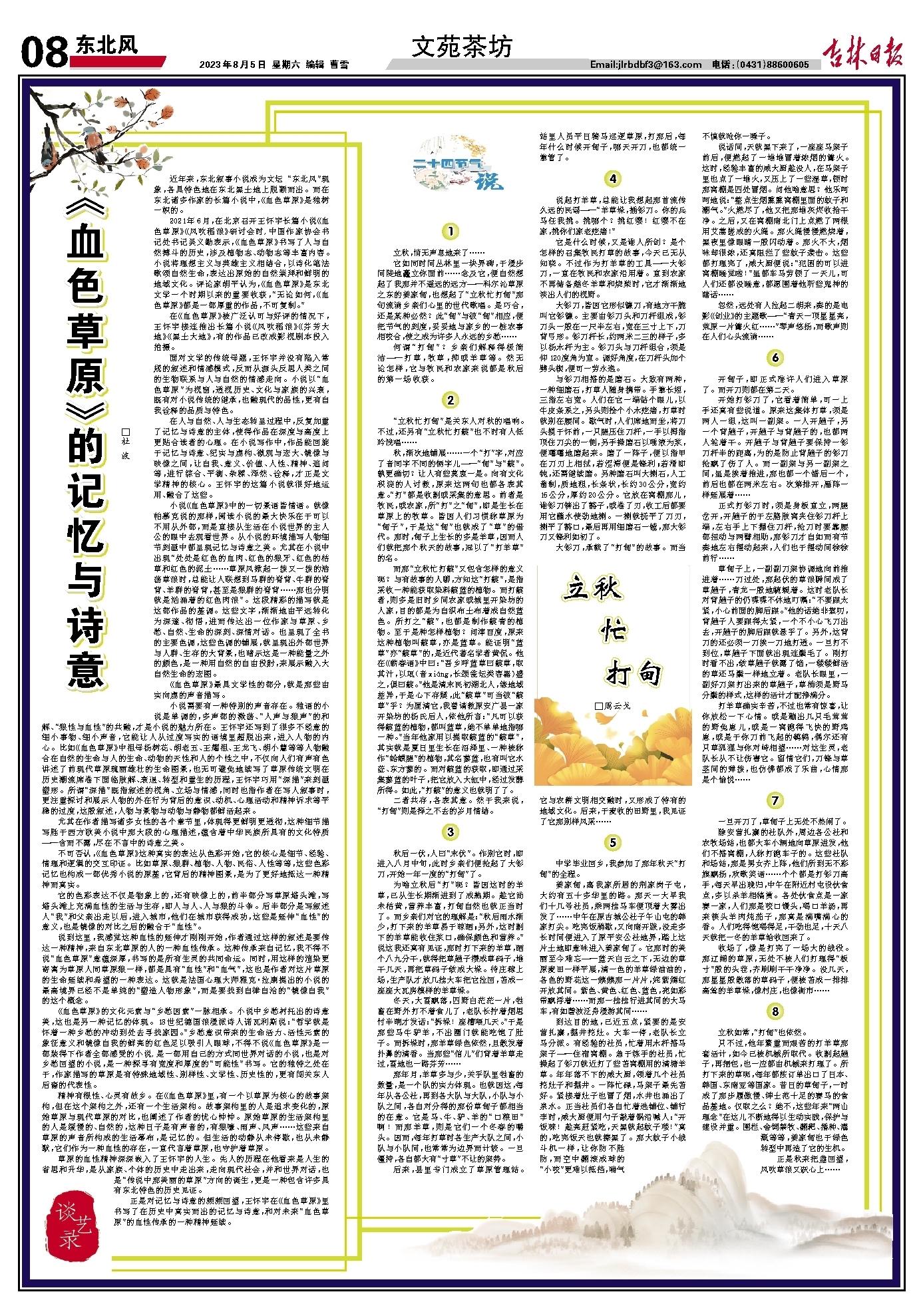近年来,东北叙事小说成为文坛 “东北风”现象,各具特色地在东北黑土地上脱颖而出。而在东北诸多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血色草原》是独树一帜的。
2021年6月,在北京召开王怀宇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研讨会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血色草原》书写了人与自然搏斗的历史,涉及植物志、动物志等丰富内容。小说将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以诗化笔法歌颂自然生命,表达出原始的自然崇拜和鲜明的地域文化。评论家胡平认为,《血色草原》是东北文学一个时期以来的重要收获,“无论如何,《血色草原》都是一部厚重的作品,不可复制。”
在《血色草原》被广泛认可与好评的情况下,王怀宇接连推出长篇小说《风吹稻浪》《芬芳大地》《黑土大地》,有的作品已改成影视剧本投入拍摄。
面对文学的传统母题,王怀宇并没有陷入常规的叙述和情感模式,反而从源头反思人类之间的生物联系与人与自然的情感走向。小说以“血色草原”为视窗,透视历史、文化与家族的兴衰,既有对小说传统的继承,也融现代的品性,更有自我诠释的品质与特色。
在人与自然、人与生态转呈过程中,反复加重了记忆与诗意的主体,使得作品在深度与高度上更贴合读者的心理。在小说写作中,作品能回旋于记忆与诗意、纪实与虚构、微观与宏大、镜像与映像之间,让自我、意义、价值、人性、精神、追问等,进行综合、平衡、杂糅、浑然、诠释,才正是文学精神的核心。王怀宇的这篇小说就很好地运用、融合了这些。
小说《血色草原》中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就像帕慕克说的那样,阅读小说的最大快乐在于可以不用从外部,而是直接从生活在小说世界的主人公的眼中去观看世界。从小说的环境描写人物细节刻画中都呈现记忆与诗意之美。尤其在小说中出现“处处是红色的血肉、红色的狼牙、红色的枯草和红色的泥土……草原风掀起一拨又一拨的浩荡草浪时,总能让人联想到马群的脊背、牛群的脊背、羊群的脊背,甚至是狼群的脊背……那也分明就是汹涌着的红色肉浪”。这段精彩的描写就是这部作品的基调。这些文字,渐渐地由平远转化为深邃、彻悟,进而传达出一位作家与草原、乡愁、自然、生命的深刻、深情对话。也呈现了全书的主要色调,这些色调的铺展,就呈现出外部世界与人群、生存的大背景,也暗示这是一种能量之外的颜色,是一种用自然的自由投射,来展示融入大自然生命的宏图。
《血色草原》最具文学性的部分,就是那些由实向虚的声音描写。
小说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存在。独语的小说是单调的,多声部的激荡、“人声与狼声”的和解、“狼性与血性”的共融,才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王怀宇还写到了很多不经意的细小事物、细小声音,它能让人从过度写实的语境里超脱出来,进入人物的内心。比如《血色草原》中祖母杨树花、胡老五、王耀祖、王龙飞、胡小慧等等人物融合在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动物的天性和人的个性之中,不仅向人们有声有色讲述了前现代草原瑰丽雄壮的生命图景,也无可避免地续写了草原传统文明在历史潮流席卷下面临肢解、衰退、转型和重生的历程,王怀宇巧用“深描”来刻画塑形。所谓“深描”既指叙述的视角、立场与情感,同时也指作者在写人叙事时,更注重探讨和展示人物的外在行为背后的意识、动机、心理活动和精神诉求等平稳的过度,这般叙述,人物与景物与动物与静物都鲜活起来。
尤其在作者描写诸多女性的各个章节里,体现得更鲜明更透彻,这种细节描写胜于西方欧美小说中那大段的心理描述,蕴含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含而不露,尽在不言中的诗意之美。
不可否认,《血色草原》这种真实的表达从色彩开始,它的核心是细节、经验、情理和逻辑的交互印证。比如草原、狼群、植物、人物、民俗、人性等等,这些色彩记忆也构成一部优秀小说的原基,它背后的精神图景,是为了更好地抵达一种精神而真实。
它的色彩表达不仅是物象上的,还有映像上的,前半部分写草原塔头滩,写塔头滩上充满血性的生活与生存,即人与人、人与狼的斗争。后半部分是写叙述人“我”和父亲出走以后,进入城市,他们在城市获得成功,这些是延伸“血性”的意义,也是镜像的对比之后的融合于“血性”。
说到这里,我感觉这种血性的延伸才刚刚开始,作者通过这样的叙述是要传达一种精神,来自东北草原的人的一种血性传承。这种传承来自记忆,我不得不说“血色草原”意蕴深厚,书写的是所有生灵的共同命运。同时,用这样的渲染更寄寓为草原人同草原狼一样,都是具有“血性”和“血气”,这也是作者对这片草原的生命延续和希望的一种表达。这就是法国心理大师雅克·拉康提出的小说的最高境界已经不是单纯的“塑造人物形象”,而是要找到自律自洽的“镜像自我”的这个概念。
《血色草原》的文化元素与“乡愁因素”一脉相承。小说中乡愁衬托出的诗意美,这也是另一种记忆的体现。18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乡愁意识带来的生命活力、活性元素的象征意义和镜像自我的鲜亮的红色足以吸引人眼球,不得不说《血色草原》是一部装得下作者全部感受的小说,是一部用自己的方式同世界对话的小说,也是对乡愁回望的小说,是一种探寻有宽度和厚度的“可能性”书写。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描写的草原是有特殊地域性、别样性、文学性、历史性的,更有闯关东人后裔的代表性。
精神有根性、心灵有故乡。在《血色草原》里,有一个以草原为核心的故事架构,但在这个架构之外,还有一个生活架构。故事架构里的人是追求变化的,原始草原与现代草原的对比,也阐述了作者的忧心忡忡。原始草原的生活架构里的人是缓慢的、自然的,这种日子是有声音的,有狼嚎、雨声、风声……这些来自草原的声音所构成的生活幕布,是记忆的。但生活的动静从未停歇,也从未静默,它们作为一种血性的存在,一直代言着草原,也守护着草原。
草原的血性精神深深嵌入了王怀宇的人生。先人的历程在他看来是人生的省思和升华,是从家族、个体的历史中走出来,走向现代社会,并和世界对话,也是“传说中那美丽的草原”方向的诞生,更是一种包含许多具有东北特色的历史见证。
正是对记忆与诗意的频频回望,王怀宇在《血色草原》里书写了在历史中真实而出的记忆与诗意,和对未来“血色草原”的血性传承的一种精神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