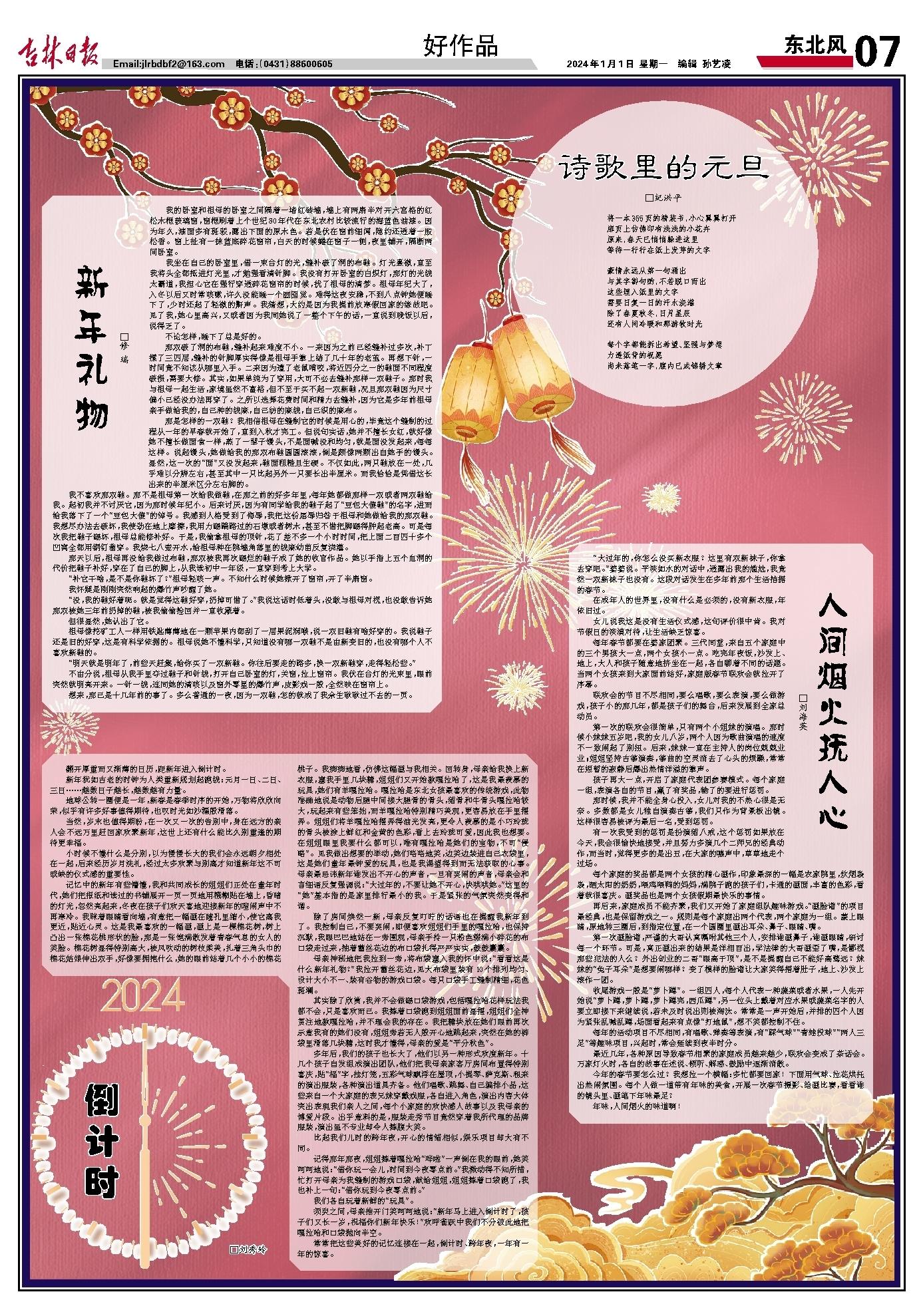“大过年的,你怎么没买新衣服?这里有双新袜子,你拿去穿吧。”婆婆说。平淡如水的对话中,透露出我的尴尬,我竟然一双新袜子也没有。这段对话发生在多年前那个生活拮据的春节。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没有新衣服,年依旧过。
女儿说我这是没有生活仪式感,这句评价很中肯。我对节假日的淡漠对待,让生活缺乏惊喜。
每年春节都要在婆家团聚。三代同堂,来自五个家庭中的三个男孩大一点,两个女孩小一点。吃完年夜饭,沙发上、地上,大人和孩子随意地挤坐在一起,各自聊着不同的话题。当两个女孩来到大家面前站好,家庭版春节联欢会就拉开了序幕。
联欢会的节目不尽相同,要么唱歌,要么表演,要么做游戏,孩子小的那几年,都是孩子们的舞台,后来发展到全家总动员。
第一次的联欢会很简单,只有两个小姐妹的演唱。那时候小妹妹五岁吧,我的女儿八岁,两个人因为歌曲演唱的速度不一致闹起了别扭。后来,妹妹一直在主持人的岗位兢兢业业;姐姐坚持古筝演奏,筝曲的空灵消去了心头的烦躁,常常在短暂的寂静后爆出热情洋溢的掌声。
孩子再大一点,开启了家庭代表团参赛模式。每个家庭一组,表演各自的节目,赢了有奖品,输了的要进行惩罚。
那时候,我并不能全身心投入,女儿对我的不热心很是无奈。多数都是女儿独自演奏古筝,我们只作为背景板出镜。这样很容易被评为最后一名,受到惩罚。
有一次我受到的惩罚是扮演猪八戒,这个惩罚如果放在今天,我会很愉快地接受,并且努力多演几个二师兄的经典动作,而当时,觉得更多的是出丑,在大家的嘘声中,草草地走个过场。
每个家庭的奖品都是两个女孩的精心画作,印象最深的一幅是农家院里,炊烟袅袅,晒太阳的奶奶,喂鸡喂鸭的妈妈,满院子跑的孩子们,卡通的画面,丰富的色彩,看着就很喜庆。画奖品也是两个女孩假期最快乐的事情。
再后来,家庭成员不能齐聚,我们又开始了家庭组队趣味游戏。“画脸谱”的项目最经典,也是保留游戏之一。规则是每个家庭出两个代表,两个家庭为一组。蒙上眼睛,原地转三圈后,到指定位置,在一个圆圈里画出耳朵、鼻子、眼睛、嘴。
第一次画脸谱,严谨的大哥认真嘱咐其他三个人,安排谁画鼻子,谁画眼睛,研讨每一个环节。可是,真正画出来的结果是洋相百出,学法律的大哥画歪了嘴,是鄙视那些犯法的人么?外出创业的二哥“眼高于顶”,是不是提醒自己不能好高骛远?妹妹的“兔子耳朵”是想要闹哪样?变了模样的脸谱让大家笑得捂着肚子,地上、沙发上滚作一团。
收尾游戏一般是“萝卜蹲”。一组四人,每个人代表一种蔬菜或者水果,一人先开始说“萝卜蹲,萝卜蹲,萝卜蹲完,西瓜蹲”,另一位头上戴着对应水果或蔬菜名字的人要立即接下来继续说,若未及时说出则被淘汰。常常是一声开始后,并排的四个人因为紧张乱喊乱蹲,场面看起来有点像“打地鼠”,想不笑都控制不住。
每年的活动项目不尽相同,有唱歌、弹奏等表演,有“踩气球”“青蛙投球”“两人三足”等趣味项目,兴起时,常会延续到夜半时分。
最近几年,各种原因导致春节相聚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少,联欢会变成了茶话会。万家灯火时,各自的故事在述说、倾听、解惑、鼓励中逐渐消散。
今年的春节要怎么过?我想拉一个横幅:多忙都要回家!下面用气球、拉花烘托出热闹氛围。每个人做一道带有年味的美食,开展一次春节摄影、绘画比赛,看看谁的镜头里、画笔下年味最足?
年味,人间烟火的味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