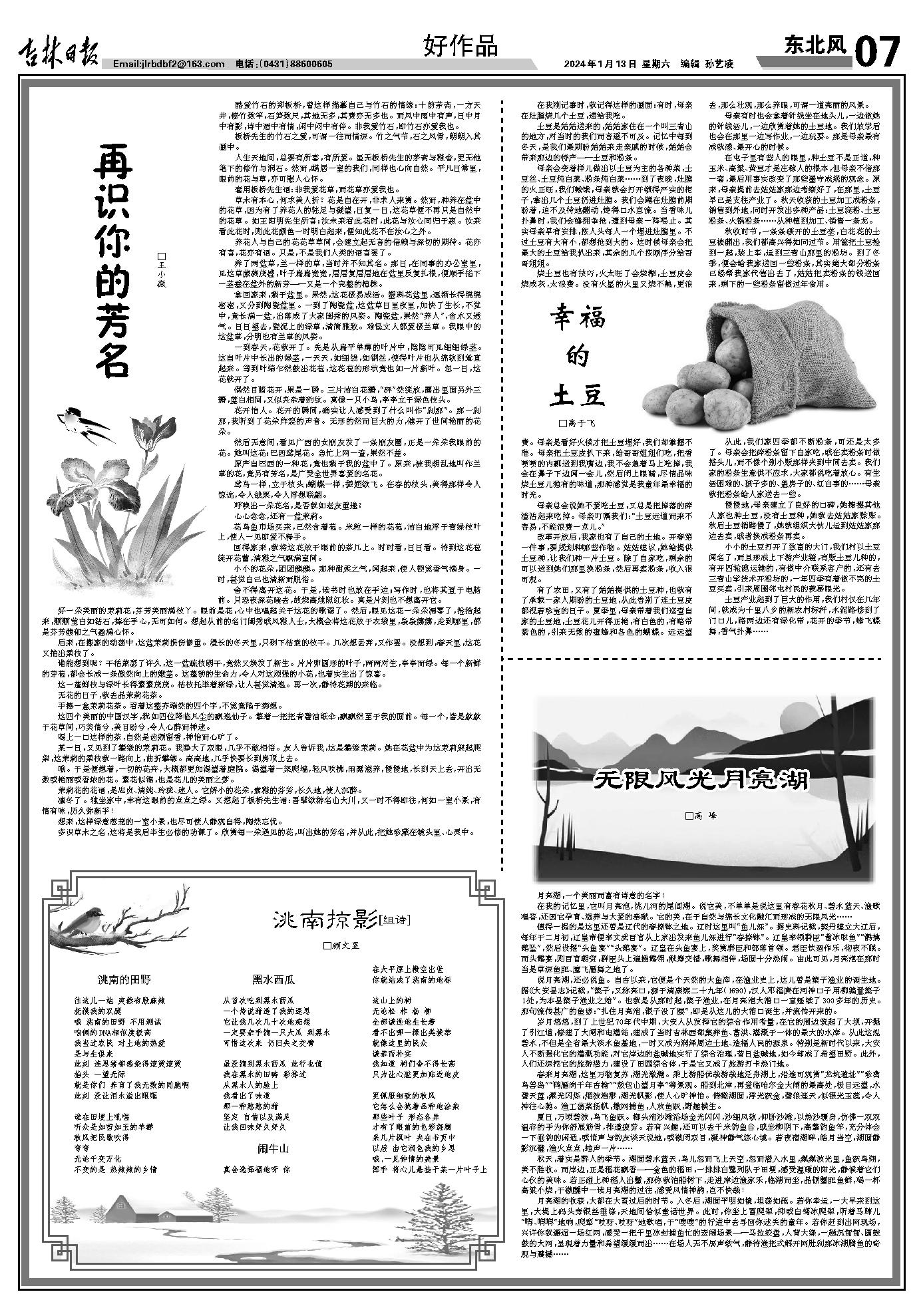在我刚记事时,就记得这样的画面:有时,母亲在灶膛烧几个土豆,递给我吃。
土豆是姑姑送来的,姑姑家住在一个叫三青山的地方,对当时的我们而言遥不可及。记忆中每到冬天,是我们最期盼姑姑来走亲戚的时候,姑姑会带来那边的特产——土豆和粉条。
母亲会变着样儿做出以土豆为主的各种菜,土豆丝、土豆炖白菜、粉条炖白菜……到了夜晚,灶膛的火正旺,我们喊饿,母亲就会打开锁得严实的柜子,拿出几个土豆扔进灶膛。我们会蹲在灶膛前期盼着,迫不及待地翻动,馋得口水直流。当香味儿扑鼻时,我们会蜂拥争抢,遭到母亲一阵喝止。其实母亲早有安排,按人头每人一个埋进灶膛里。不过土豆有大有小,都想抢到大的。这时候母亲会把最大的土豆给我扒出来,其余的几个按顺序分给哥哥姐姐。
烧土豆也有技巧,火太旺了会烧糊,土豆皮会烧成灰,太浪费。没有火星的火里又烧不熟,更浪费。母亲是看好火候才把土豆埋好,我们却掌握不准。母亲把土豆皮扒下来,给哥哥姐姐们吃,把香喷喷的内瓤送到我嘴边,我不会急着马上吃掉,我会在鼻子下边闻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尽情品味烧土豆儿独有的味道,那种感觉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
母亲总会说她不爱吃土豆,又总是把掉落的碎渣沾起来吃掉。母亲叮嘱我们:“土豆远道而来不容易,不能浪费一点儿。”
改革开放后,我家也有了自己的土地。开春第一件事,要规划种哪些作物。姑姑建议,她给提供土豆种,让我们种一片土豆。除了自家吃,剩余的可以送到她们那里换粉条,然后再卖粉条,收入很可观。
有了农田,又有了姑姑提供的土豆种,也就有了承载一家人期盼的土豆地,从此告别了连土豆皮都视若珍宝的日子。夏季里,母亲带着我们巡查自家的土豆地,土豆花儿开得正艳,有白色的,有略带紫色的,引来无数的蜜蜂和各色的蝴蝶。远远望去,那么壮观,那么养眼,可谓一道亮丽的风景。
母亲有时也会拿着针线坐在地头儿,一边做她的针线活儿,一边欣赏着她的土豆地。我们放学后也会在那里一边写作业,一边玩耍。那是母亲最有成就感、最开心的时候。
在屯子里有些人的眼里,种土豆不是正道,种玉米、高粱、黄豆才是庄稼人的根本,但母亲不信那一套,最后用事实改变了那些墨守成规的观念。原来,母亲提前去姑姑家那边考察好了,在那里,土豆早已是支柱产业了。秋天收获的土豆加工成粉条,销售到外地,同时开发出多种产品:土豆淀粉、土豆粉条、火锅粉条……从种植到加工、销售一条龙。
秋收时节,一条条破开的土豆垄,白花花的土豆被翻出,我们都高兴得如同过节。用筐把土豆捡到一起,装上车,运到三青山那里的粉坊。到了冬季,便会给我家送回一些粉条,其实绝大部分粉条已经帮我家代售出去了,姑姑把卖粉条的钱送回来,剩下的一些粉条留做过年食用。
从此,我们家四季都不断粉条,可还是太多了。母亲会把碎粉条留下自家吃,或在卖粉条时做搭头儿,而不像个别小贩那样夹到中间去卖。我们家的粉条生意供不应求,大家都说吃着放心。有生活困难的、孩子多的、盖房子的、红白事的……母亲就把粉条给人家送去一些。
慢慢地,母亲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她撺掇其他人家也种土豆,没有土豆种,她就去姑姑家赊账。秋后土豆销路慢了,她就组织大伙儿运到姑姑家那边去卖,或者换成粉条再卖。
小小的土豆打开了致富的大门,我们村以土豆闻名了,而且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有贩土豆儿种的,有开四轮跑运输的,有做中介联系客户的,还有去三青山学技术开粉坊的,一年四季有着做不完的土豆买卖,引来周围邻屯村民的羡慕眼光。
土豆产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村仅在几年间,就成为十里八乡的新农村标杆,水泥路修到了门口儿,路两边还有绿化带,花开的季节,蜂飞蝶舞,香气扑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