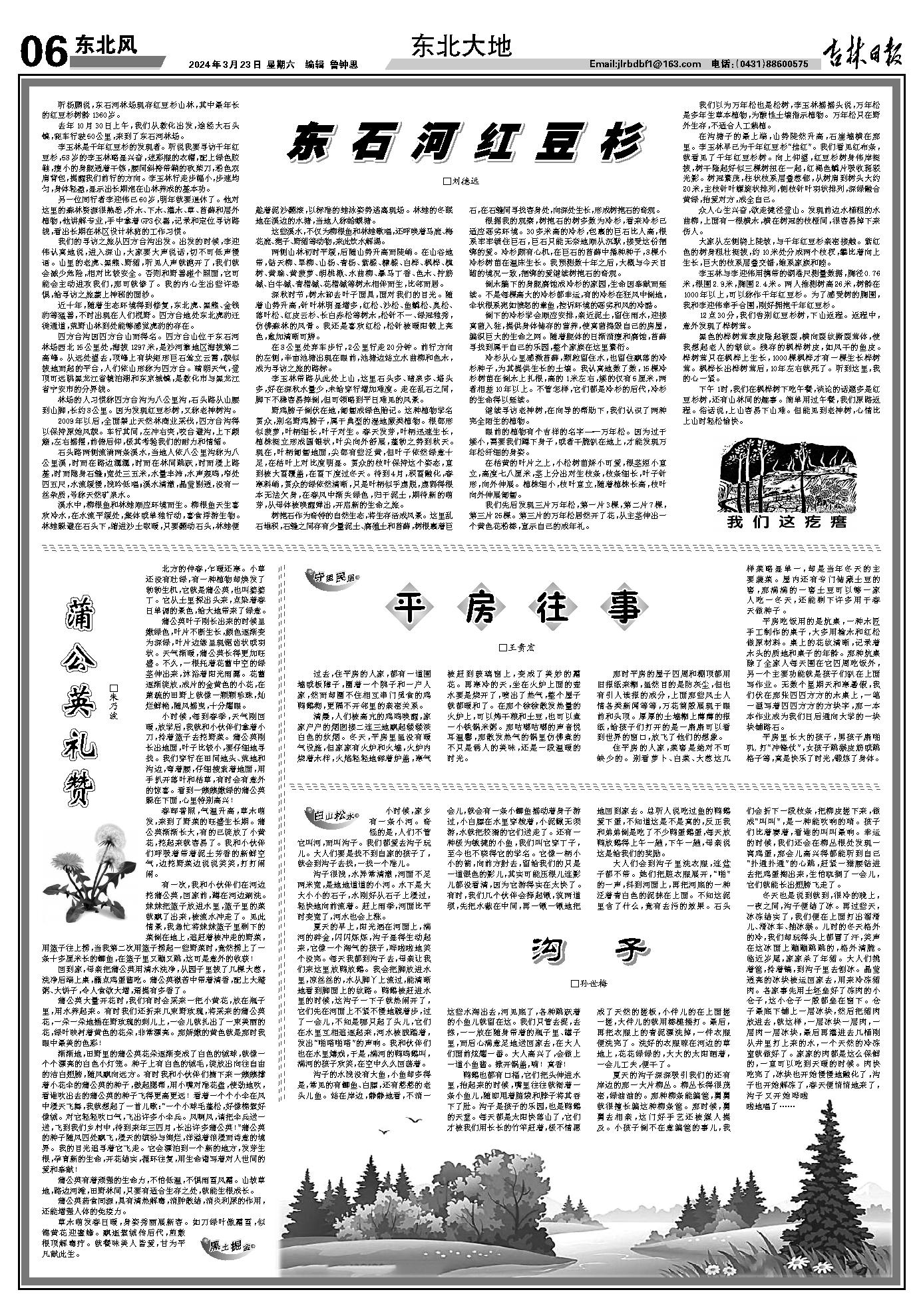过去,住平房的人家,都有一道围墙或板障子,圈着一个院子和一户人家,然而却圈不住相互串门觅食的鸡鸭鹅狗,更隔不开邻里的亲密关系。
清晨,人们被高亢的鸡鸣唤醒,家家户户的烟囱接二连三地飘起缕缕淡白色的炊烟。冬天,平房里虽没有暖气设施,但家家有火炉和火墙,火炉内烧着木柈,火焰轻轻地舔着炉盖,寒气被赶到玻璃窗上,变成了美妙的霜花。再寒冷的天,坐在火炉上面的壶水要是烧开了,喷出了热气,整个屋子就都暖和了。在那个徐徐散发热量的火炉上,可以烤干粮和土豆,也可以煮一小铁锅米粥。那咕嘟咕嘟的声音悦耳温馨,那散发热气的锅里仿佛煮的不只是诱人的美味,还是一段温暖的时光。
那时平房的屋子四周和棚顶都用旧报纸来糊,虽然目的是防灰尘,但也有引人读报的成分,上面那些风土人情各类新闻等等,万花筒般展现于眼前和头顶。厚厚的土墙糊上薄薄的报纸,给孩子们打开的是一扇扇可以看到世界的窗口,放飞了他们的想象。
住平房的人家,菜窖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别看萝卜、白菜、大葱这几样菜略显单一,却是当年冬天的主要蔬菜。屋内还有专门储藏土豆的窖,那满满的一窖土豆可以够一家人吃一冬天,还能剩下许多用于春天做种子。
平房吃饭用的是炕桌,一种木匠手工制作的桌子,大多用榆木和红松做原材料。桌上的花纹清晰,记录着木头的质地和桌子的年龄。那种炕桌除了全家人每天围在它四周吃饭外,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孩子们趴在上面写作业。无数个星期天和寒暑假,我们伏在那张四四方方的木桌上,一笔一画写着四四方方的方块字,那一本本作业成为我们日后通向大学的一块块铺路石。
平房里长大的孩子,男孩子扇啪叽,打“冲锋仗”,女孩子跳猴皮筋或跳格子等,真是快乐了时光,锻炼了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