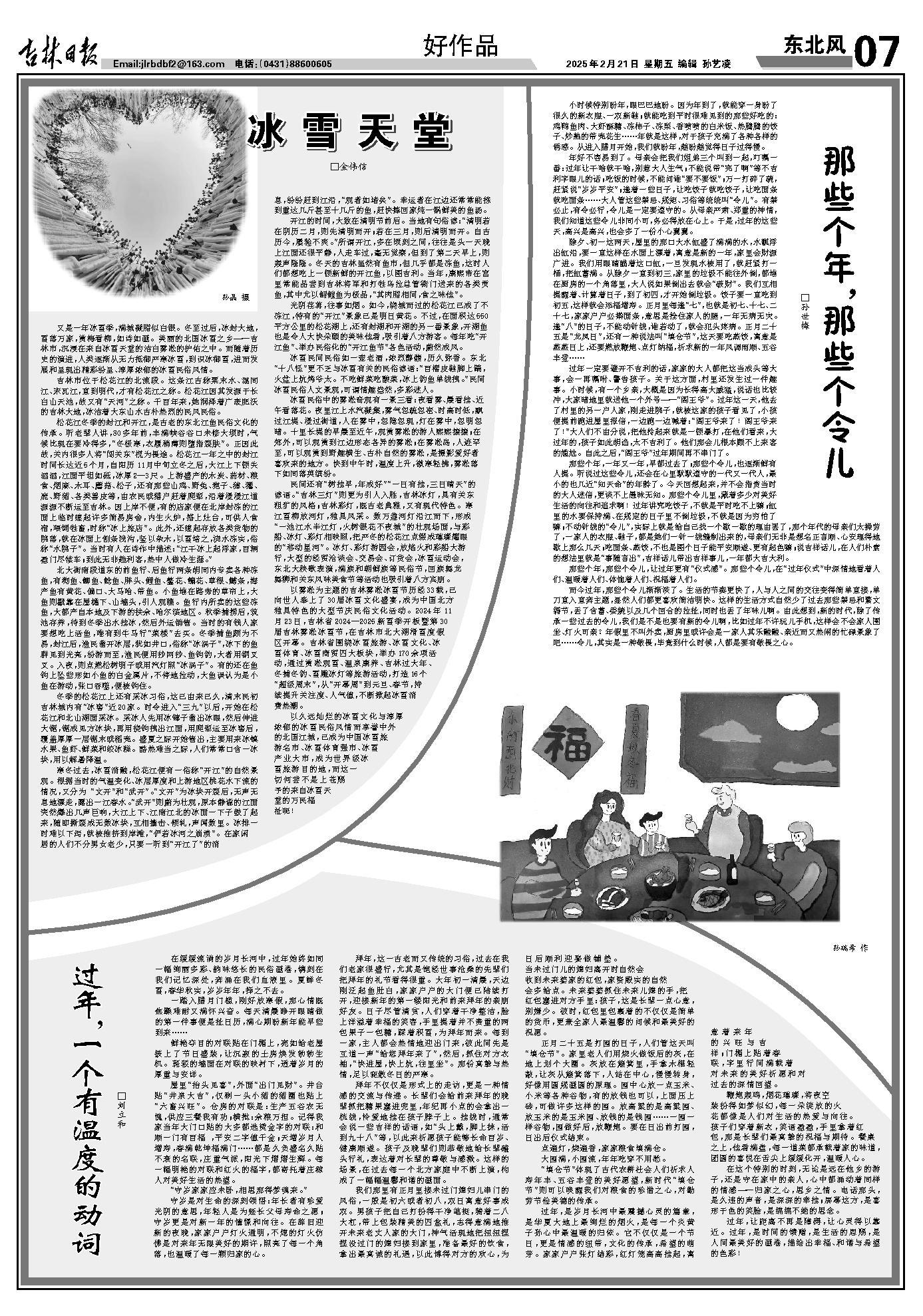在缓缓流淌的岁月长河中,过年始终如同一幅绚丽多彩、韵味悠长的民俗画卷,镌刻在我们记忆深处,奔涌在我们血液里。夏蝉冬雪,春华秋实,岁岁年年,挥之不去。
一踏入腊月门槛,刚好放寒假,那心情既焦躁难耐又满怀兴奋。每天清晨睁开眼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扯日历,满心期盼新年能早些到来……
鲜艳夺目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宛如给老屋披上了节日盛装,让沉寂的土房焕发勃勃生机。斑驳的墙面在对联的映衬下,透着岁月的厚重与安详。
屋里“抬头见喜”,外面“出门见财”。井台贴“井泉大吉”,仅剩一头小猪的猪圈也贴上“六畜兴旺”。仓房的对联是:生产五谷农无愧,供应三餐我有功;横批:余粮万担。记得我家当年大门口贴的大多都选烫金字的对联:和顺一门有百福 ,平安二字值千金;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都是久负盛名久贴不衰的名联,庄重气派,阳光下熠熠生辉。每一幅明艳的对联和红火的福字,都寄托着庄稼人对美好生活的热望。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守岁是对生命的深刻领悟:年长者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是为延长父母寿命之愿;守岁更是对新一年的憧憬和向往。在辞旧迎新的夜晚,家家户户灯火通明,不熄的灯火仿佛是对来年无限美好的期许,照亮了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颗归家的心。
拜年,这一古老而又传统的习俗,过去在我们老家很盛行,尤其是饱经世事沧桑的先辈们把拜年的礼节看得很重。大年初一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家家户户的大门便已陆续打开,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和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日子尽管清贫,人们穿着干净整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手里提着并不贵重的两包果子一包糖,踩着积雪,为拜年而来。每到一家,主人都会热情地迎出门来,彼此间先是互道一声“给您拜年来了”,然后,抓住对方衣袖,“快进屋,快上炕,往里坐”。那份真挚与热情,足以驱散冬日的严寒。
拜年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走访,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与传递。长辈们会给前来拜年的晚辈抓把糖果塞进兜里,年纪再小点的会拿出一桄线,怜爱地挂在孩子脖子上。挂线时,通常会说一些吉祥的话语,如“头上戴,脚上抹,活到九十八”等,以此来祈愿孩子能够长命百岁、健康顺遂。孩子及晚辈们则恭敬地给长辈磕头行礼,表达着对长辈的尊敬与感激。这样的场景,在过去每一个北方家庭中不断上演,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
我们那里有正月里接未过门媳妇儿串门的风俗,一般是初六或者初八,双日寓意好事成双。男孩子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笔挺,骑着二八大杠,带上包装精美的四盒礼,志得意满地推开未来老丈人家的大门,神气活现地把扭扭捏捏没过门的媳妇接到家里,准备最好的饮食,拿出最真诚的礼遇,以此博得对方的欢心,为日后顺利迎娶做铺垫。当未过门儿的媳妇离开时自然会收到未来婆家的红包,家资殷实的自然会多给点。未来婆婆抓住未来儿媳的手,把红包塞进对方手里:孩子,这是长辈一点心意,别嫌少。彼时,红包里包裹着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货币,更兼全家人最温馨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正月二十五是打囤的日子,人们管这天叫“填仓节”。家里老人们用烧火做饭后的灰,在地上划个大圈。灰放在簸箕里,手拿木棍轻敲,让灰从簸箕落下,人站在中心,慢慢转身,好像用圆规画圆的原理。囤中心放一点玉米、小米等各种谷物,有的放钱也可以,上面压上砖,可做许多这样的囤。放高粱的是高粱囤、放玉米的是玉米囤、放钱的是钱囤……一囤一样谷物,囤做好后,放鞭炮。要在日出前打囤,日出后仪式结束。
点遍灯,烧遍香,家家粮食填满仓。
大囤满,小囤流,年年吃穿不用愁。
“填仓节”体现了古代农耕社会人们祈求人寿年丰、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新时代“填仓节”则可以唤醒我们对粮食的珍惜之心,对勤劳节俭美德的传承。
过年,是岁月长河中最震撼心灵的篇章,是华夏大地上最绚烂的烟火,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心中最温暖的归依。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情感的纽带,文化的传承,希望的萌芽。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红灯笼高高挂起,寓意着来年的兴旺与吉祥;门楣上贴着春联,字里行间满载着对未来的美好祈愿和对过去的深情回望。
鞭炮轰鸣,烟花璀璨,将夜空装扮得如梦似幻,每一朵绽放的火花都像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孩子们穿着新衣,笑语盈盈,手里拿着红包,那是长辈们最真挚的祝福与期待。餐桌之上,佳肴满盘,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的味道,团圆的喜悦在舌尖上缓缓化开,温暖人心。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无论是远在他乡的游子,还是守在家中的亲人,心中都涌动着同样的情感——归家之心,思乡之情。电话那头,是久违的声音,是深深的牵挂;屏幕这方,是喜形于色的笑脸,是绵绵不绝的思念。
过年,让距离不再是障碍,让心灵得以靠近。过年,是时间的馈赠,是生活的恩赐,是人间最美好的画卷,描绘出幸福、和谐与希望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