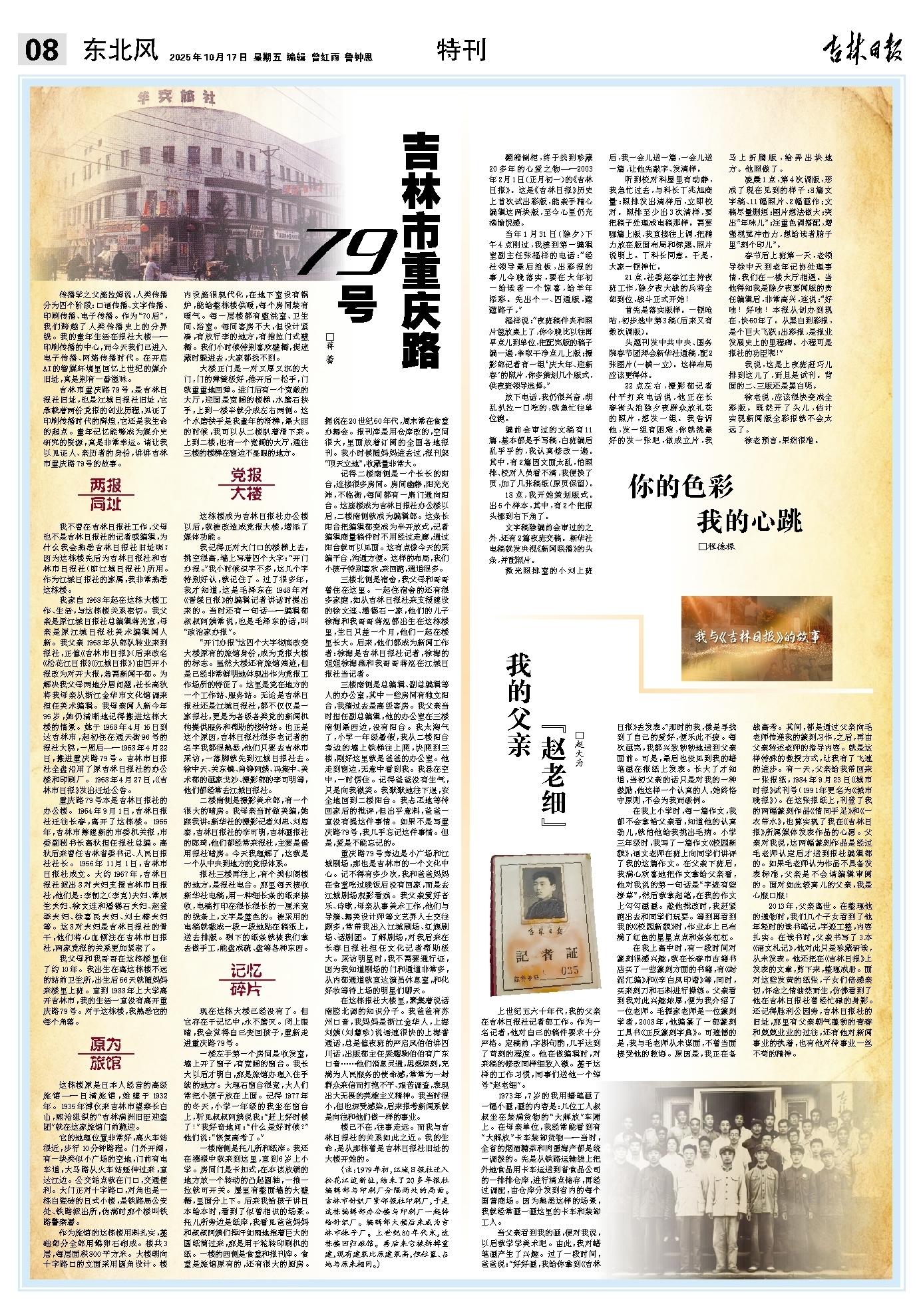传播学之父施拉姆说,人类传播分为四个阶段: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作为“70后”,我们跨越了人类传播史上的分界线。我的童年生活在报社大楼——印刷传播的中心,而今天我们已进入电子传播、网络传播时代。在开启AI的智媒环境里回忆上世纪的媒介旧址,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吉林市重庆路79号,是吉林日报社旧址,也是江城日报社旧址,它承载着两份党报的创业历程,见证了印刷传播时代的辉煌,它还是我生命的起点。童年记忆能够成为媒介史研究的资源,真是非常幸运。请让我以见证人、亲历者的身份,讲讲吉林市重庆路79号的故事。
两报
同址
我不曾在吉林日报社工作,父母也不是吉林日报社的记者或编辑,为什么我会熟悉吉林日报社旧址呢?因为这栋楼先后为吉林日报社和吉林市日报社(即江城日报社)所用。作为江城日报社的家属,我非常熟悉这栋楼。
我家自1958年起在这栋大楼工作、生活,与这栋楼关系密切。我父亲是原江城日报社总编辑蒋光宜,母亲是原江城日报社美术编辑闻人新。我父亲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到报社,正值《吉林市日报》(后来改名《松花江日报》《江城日报》)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急需新闻干部。为解决我父母两地分居问题,社长高狄将我母亲从浙江金华市文化馆调来担任美术编辑。我母亲闻人新今年95岁,她仍清晰地记得搬进这栋大楼的情景。她于1958年4月15日到达吉林市,起初住在通天街96号的报社大院,一周后——1958年4月22日,搬进重庆路79号。吉林市日报社全盘沿用了原吉林日报社的办公楼和印刷厂。1958年4月27日,《吉林市日报》发出迁址公告。
重庆路79号本是吉林日报社的办公楼。1954年9月1日,吉林日报社迁往长春,离开了这栋楼。1955年,吉林市筹建新的市委机关报,市委副秘书长高狄担任报社总编。高狄后来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人民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1日,吉林市日报社成立。大约1957年,吉林日报社派出8对夫妇支援吉林市日报社,他们是:李韧之(李克)夫妇、常辰生夫妇、徐文连和潘锡石夫妇、赵登举夫妇、徐喜民夫妇、刘士椿夫妇等。这8对夫妇是吉林日报社的骨干,他们将心血倾注在吉林市日报社,两家党报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我父母和我哥哥在这栋楼里住了约10年。我出生在离这栋楼不远的站前卫生所,出生后56天就随妈妈来楼里上班。直到1988年上大学离开吉林市,我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重庆路79号。对于这栋楼,我熟悉它的每个角落。
原为
旅馆
这栋楼原是日本人经营的高级旅馆——日清旅馆,始建于1932年。1935年溥仪来吉林市望祭长白山,熙洽组织的“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就在这家旅馆门前跪迎。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离火车站很近,步行10分钟路程。门外开阔,有一块类似小广场的空地,门前有电车道,大马路从火车站延伸过来,直达江边。公交站点就在门口,交通便利。大门正对十字路口,对角也是一栋白瓷砖的日式小楼,是铁路局公安处、铁路派出所,伪满时那个楼叫铁路警察署。
作为旅馆的这栋楼用料扎实,基础部分全部用鹅卵石砌成。楼共3层,每层面积800平方米。大楼朝向十字路口的立面采用圆角设计。楼内设施很现代化,在地下室设有锅炉,能给整栋楼供暖,每个房间装有暖气。每一层楼都有盥洗室、卫生间、浴室。每间客房不大,但设计紧凑,有放行李的地方,有推拉门式壁橱。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壁橱,捉迷藏时躲进去,大家都找不到。
大楼正门是一对又厚又沉的大门,门的弹簧极好,推开后一松手,门就重重地回弹。进门后有一个宽敞的大厅,迎面是宽阔的楼梯,水磨石扶手,上到一楼半就分成左右两侧。这个水磨扶手是我童年的滑梯,最大胆的时候,我可以从二楼趴着滑下来。上到二楼,也有一个宽阔的大厅,通往三楼的楼梯在窗边不显眼的地方。
党报
大楼
这栋楼成为吉林日报社办公楼以后,就被改造成党报大楼,增添了媒体功能。
我记得正对大门口的楼梯上去,挑空很高,墙上写着四个大字:“开门办报。”我小时候识字不多,这几个字特别好认,就记住了。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的编辑记者讲话时提出来的。当时还有一句话——编辑部叔叔阿姨常说,也是毛泽东的话,叫“政治家办报”。
“开门办报”这四个大字彻底改变大楼原有的旅馆身份,成为党报大楼的标志。虽然大楼还有旅馆痕迹,但是已经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作为党报工作场所的特征了。这里是党在地方的一个工作站、服务站。无论是吉林日报社还是江城日报社,都不仅仅是一家报社,更是为各级各类党的新闻机构提供服务和帮助的接待站。也正是这个原因,吉林日报社很多老记者的名字我都很熟悉,他们只要去吉林市采访,一落脚就先到江城日报社去。徐中天、关东镇、肖铮阿姨、冯集中、美术部的画家戈沙、摄影部的李可明等,他们都经常去江城日报社。
二楼南侧是摄影美术部,有一个很大的暗房。我母亲当时做美编,她跟我讲: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刘忠、刘恩泰,吉林日报社的李可明,吉林画报社的郎琦,他们都经常来报社,主要是借用报社暗房。今天我理解了,这就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体系。
报社三楼再往上,有个类似阁楼的地方,是报社电台。那里每天接收新华社电稿,用一种细长条的纸来接收,电稿打印在很长很长的一厘米宽的线条上,文字是蓝色的。被采用的电稿就截成一段一段地贴在稿纸上,送去排版。剩下的纸条就被我们拿去做手工,能盘成碗、盘等各种东西。
记忆
碎片
现在这栋大楼已经没有了。但它存在于记忆中,永不磨灭。闭上眼睛,我会觉得自己变回孩子,重新走进重庆路79号。
一楼左手第一个房间是收发室,墙上开了窗子,有宽阔的窗台。我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旅馆办理入住手续的地方。大理石窗台很宽,大人们常把小孩子放在上面。记得1977年的冬天,小学一年级的我坐在窗台上,听见叔叔阿姨说我:“赶上好时候了!”我好奇地问:“什么是好时候?”他们说:“恢复高考了。”
一楼南侧是托儿所和纸库。我还在襁褓中就来到这里,直到6岁上小学。房间门是卡扣式,在本该放锁的地方放一个转动的凸起圆轴,一推一拉就可开关。屋里有整面墙的大壁橱,里面分上下。后来我给孩子讲日本绘本时,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场景。托儿所旁边是纸库,我看见爸爸妈妈和叔叔阿姨们挥汗如雨地推着巨大的圆纸筒过来,那是用于轮转印刷机的纸。一楼的西侧是食堂和报刊库。食堂是旅馆原有的,还有很大的厨房。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周末常在食堂办舞会。报刊库是用仓库改的,空间很大,里面放着订阅的全国各地报刊。我小时候随妈妈进去过,报刊架“顶天立地”,收藏量非常大。
记得二楼南侧是一个长长的阳台,连接很多房间。房间幽静,阳光充沛,不临街,每间都有一扇门通向阳台。这座楼成为吉林日报社办公楼以后,二楼南侧就成为编辑部。这条长阳台把编辑部变成为半开放式,记者编辑商量稿件时不用经过走廊,通过阳台就可以见面。这有点像今天的采编平台,沟通方便。这样的布局,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来回跑,通道很多。
三楼北侧是宿舍,我父母和哥哥曾住在这里。一起住宿舍的还有很多家庭,如从吉林日报社来支援建设的徐文连、潘锡石一家,他们的儿子徐海和我哥哥蒋泓都出生在这栋楼里,生日只差一个月,他们一起在楼里长大。后来,他们都成为新闻工作者:徐海是吉林日报社记者,徐海的姐姐徐海燕和我哥哥蒋泓在江城日报社当记者。
三楼南侧是总编辑、副总编辑等人的办公室,其中一些房间有独立阳台,我猜过去是高级客房。我父亲当时担任副总编辑,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南侧最西边,没有阳台。我太淘气了,小学一年级暑假,我从二楼阳台旁边的墙上铁梯往上爬,快爬到三楼,刚好这里就是爸爸的办公室。他走到窗边,无意中看到我。我悬在空中,一时愣住。记得爸爸没有生气,只是向我微笑。我默默地往下退,安全地回到二楼阳台。我忐忑地等待回家后的批评,但出乎意料,爸爸一直没有提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写重庆路79号,我几乎忘记这件事情。但是,爱是不能忘记的。
重庆路79号旁边是小广场和江城剧场,那也是吉林市的一个文化中心。记不得有多少次,我和爸爸妈妈在食堂吃过晚饭后没有回家,而是去江城剧场观影看戏。我父亲爱好音乐、诗歌,母亲从事美术工作,他们与导演、舞美设计师等文艺界人士交往颇多,常带我出入江城剧场、红旗剧场、话剧团。了解剧场,对我后来在长春日报社担任文化记者帮助极大。采访明星时,我不需要通行证,因为我知道剧场的门和通道非常多,从内部通道就直达演员休息室,和化好妆等待上场的明星们聊天。
在这栋报社大楼里,聚集着说话南腔北调的知识分子。我爸爸有苏州口音,我妈妈是浙江金华人,上海刘姨(刘慧珍)说语速很快的上海普通话,总是值夜班的严启凤伯伯讲四川话,出版部主任梁耀驹伯伯有广东口音……他们消息灵通,思想深刻,充满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常常为一封群众来信而打抱不平、艰苦调查,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当时很小,但也深受感染,后来报考新闻系就是向往和他们做一样的事业。
楼已不在,往事走远。而我与吉林日报社的关系如此之近。我的生命,是从那栋曾是吉林日报社旧址的大楼开始的。
(注:1979年初,江城日报社迁入松花江边新址,结束了20多年报社编辑部与印刷厂分隔两处的局面。吉林市针织厂紧邻报社印刷厂,于是这栋编辑部办公楼与印刷厂一起转给针织厂。编辑部大楼后来成为吉林市袜子厂。上世纪80年代末,这栋楼回归旅馆。再后来它被拆掉重建,现有建筑比原建筑高,但位置、占地与原来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