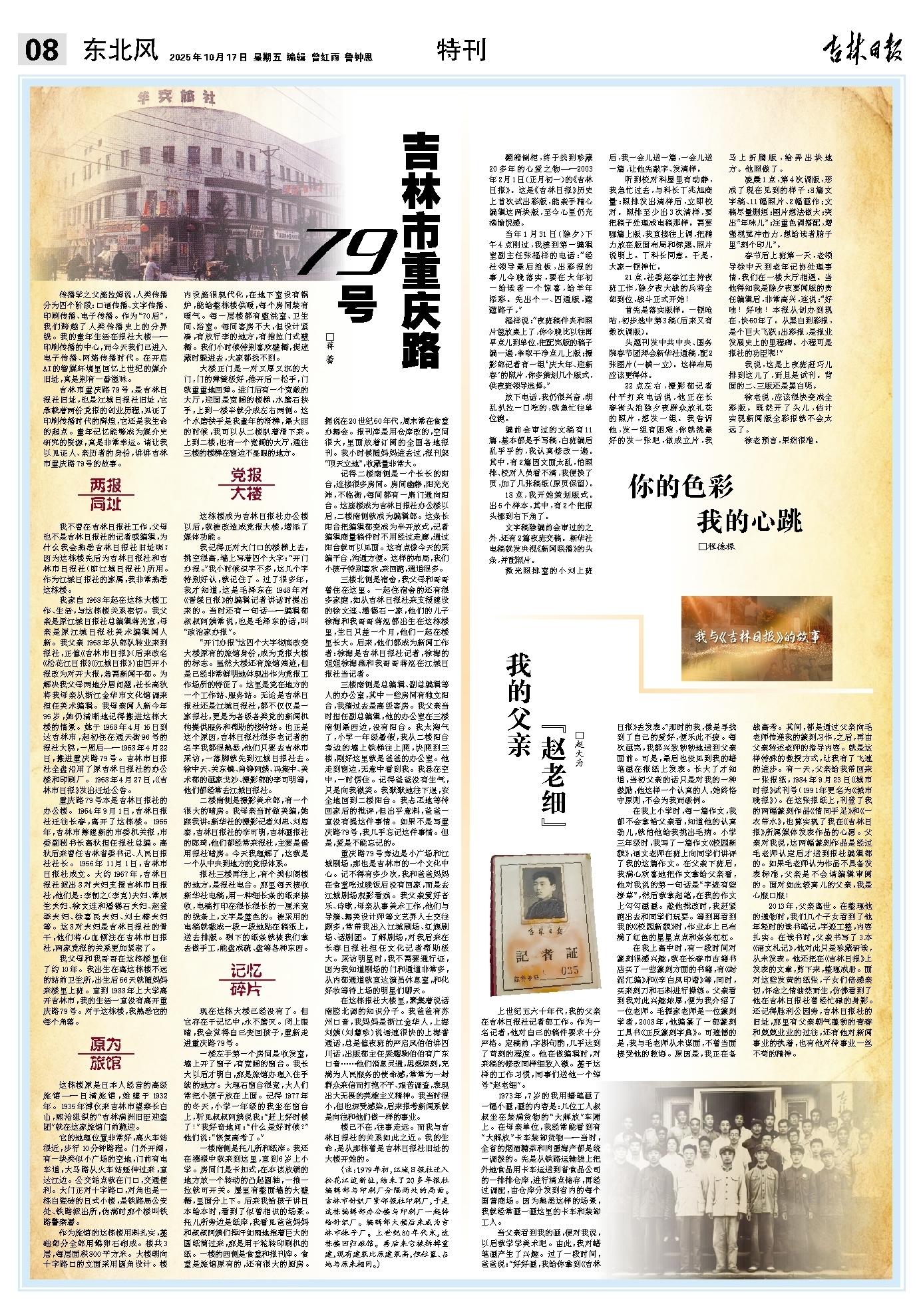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父亲在吉林日报社记者部工作。作为一名记者,他对自己的稿件要求十分严格。定稿前,字斟句酌,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他在做编辑时,对来稿的修改同样细致入微。基于这样的工作习惯,同事们送他一个绰号“赵老细”。
1973年,7岁的我用蜡笔画了一幅小画,画的内容是:几位工人叔叔坐在装满货物的“大解放”车厢上。在母亲单位,我经常能看到有“大解放”卡车装卸货物——当时,全省的烟酒糖茶和肉蛋海产都是统一调拨的。先是从铁路运输线上把外地食品用卡车运送到省食品公司的一排排仓库,进行清点储存,再经过调配,由仓库分发到省内的每个国营商场。因为熟悉这样的场景,我就经常画一画这里的卡车和装卸工人。
当父亲看到我的画,便对我说,以后就学学美术吧。由此,我对蜡笔画产生了兴趣。过了一段时间,爸爸说:“好好画,我给你拿到《吉林日报》去发表。”那时的我,像是寻找到了自己的爱好,便乐此不疲。每次画完,我都兴致勃勃地送到父亲面前。可是,最后也没见到我的蜡笔画在报纸上发表。长大了才知道,当初父亲的话只是对我的一种鼓励,他这样一个认真的人,始终恪守原则,不会为我而破例。
在我上小学时,每一篇作文,我都不会拿给父亲看,知道他的认真劲儿,就怕他给我挑出毛病。小学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校园新貌》,语文老师在班上向同学们讲评了我的这篇作文。在父亲下班后,我满心欢喜地把作文拿给父亲看,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字迹有些潦草”,然后就拿起笔,在我的作文上勾勾画画。趁他批改时,我赶紧跑出去和同学们玩耍。等到再看到我的《校园新貌》时,作业本上已布满了红色的星星点点和条条杠杠。
在我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对篆刻很感兴趣,就在长春市古籍书店买了一些篆刻方面的书籍,有《封泥汇编》和《李白凤印谱》等,同时,买来刻刀和石料进行操练。父亲看到我对此兴趣浓厚,便为我介绍了一位老师。毛振家老师是一位篆刻学者,2008年,他编纂了一部篆刻工具书《正反篆刻字典》。可遗憾的是,我与毛老师从未谋面,不曾当面接受他的教诲。原因是,我正在备战高考。其间,都是通过父亲向毛老师传递我的篆刻习作,之后,再由父亲转述老师的指导内容。就是这样特殊的教授方式,让我有了飞速的进步。有一天,父亲给我带回来一张报纸,1984年9月23日《城市时报》试刊号(1991年更名为《城市晚报》)。在这张报纸上,刊登了我的两幅篆刻作品《情同手足》和《一衣带水》,也算实现了我在《吉林日报》所属媒体发表作品的心愿。父亲对我说,这两幅篆刻作品是经过毛老师认定后才送到报社编辑部的。如果毛老师认为作品不具备发表标准,父亲是不会请编辑审阅的。面对如此较真儿的父亲,我是心服口服!
2013年,父亲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们几个子女看到了他年轻时的读书笔记,字迹工整,内容扎实。在读书时,父亲书写了3本《语文札记》,他对此只是珍藏研读,从未发表。他还把在《吉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剪下来,整理成册。面对这些发黄的纸张,子女们倍感亲切,怀念之情油然而生,仿佛看到了他在吉林日报社曾经忙碌的身影。还记得胜利公园旁,吉林日报社的旧址,那里有父亲朝气蓬勃的青春和兢兢业业的过往,还有他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也有他对待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