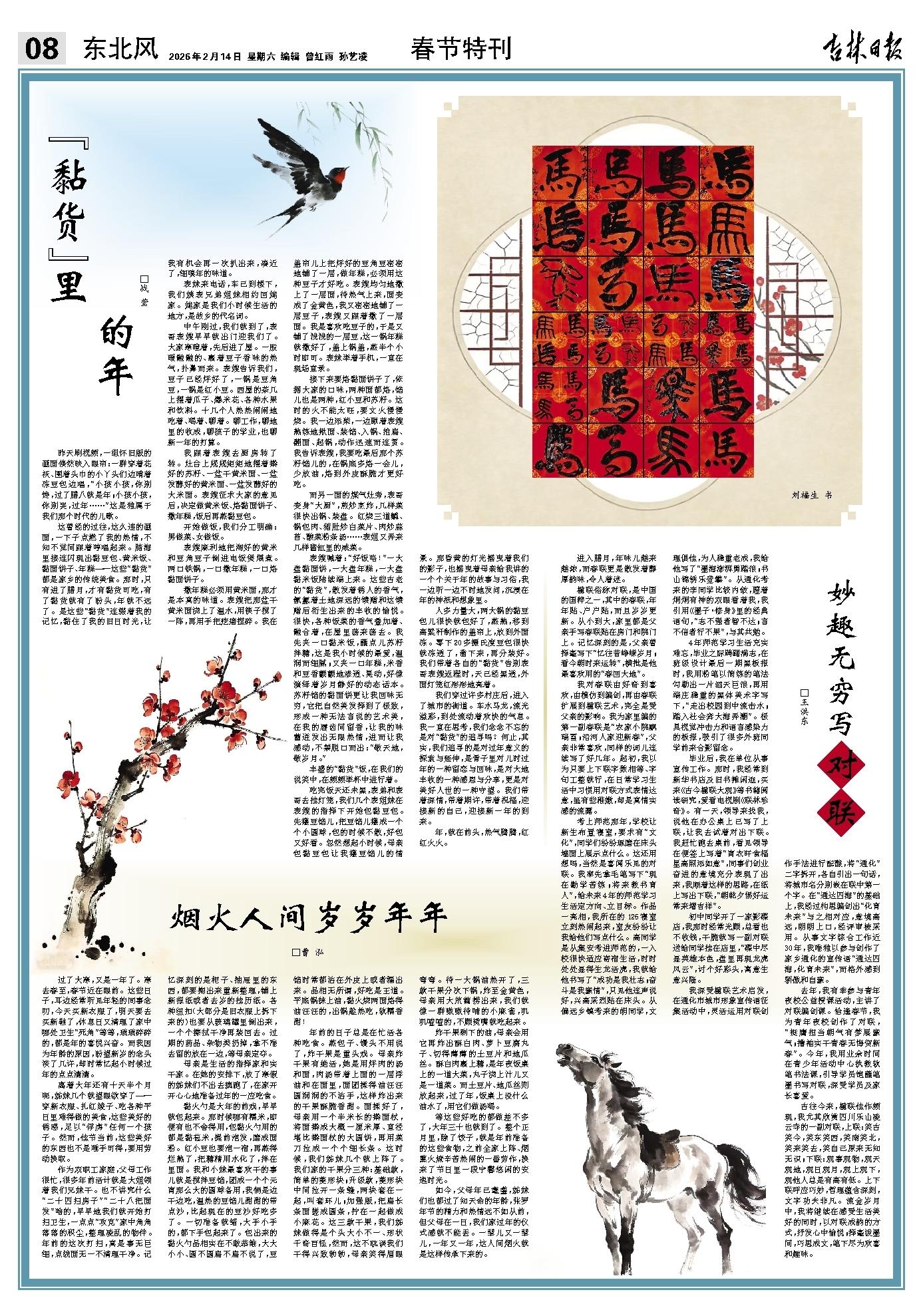昨天刷视频,一组怀旧版的画面倏然映入眼帘:一群穿着花袄、围着头巾的小丫头们边啃着冻豆包边唱,“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哭,过年……”这是独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儿歌。
这曾经的过往,这久违的画面,一下子点燃了我的热情,不知不觉间跟着哼唱起来。脑海里接连闪现出黏豆包、黄米饭、黏面饼子、年糕——这些“黏货”都是家乡的传统美食。那时,只有进了腊月,才有黏货可吃,有了黏货就有了盼头,年就不远了。是这些“黏货”连缀着我的记忆,黏住了我的旧日时光,让我有机会再一次扒出来,凑近了,细嗅年的味道。
表妹来电话,车已到楼下,我们姨表兄弟姐妹相约回姥家。姥家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故乡的代名词。
中午刚过,我们就到了,表哥表嫂早早就出门迎我们了。大家寒暄着,先后进了屋。一股暖融融的、裹着豆子香味的热气,扑鼻而来。表嫂告诉我们,豆子已经烀好了,一锅是豆角豆,一锅是红小豆。西屋的茶几上摆着瓜子、爆米花、各种水果和饮料。十几个人热热闹闹地吃着、喝着、聊着。聊工作,聊地里的收成,聊孩子的学业,也聊新一年的打算。
我跟着表嫂去厨房转了转。灶台上规规矩矩地摆着擀好的苏籽、一盆干黄米面、一盆发酵好的黄米面、一盆发酵好的大米面。表嫂征求大家的意见后,决定做黄米饭、烙黏面饼子、撒年糕,饭后再蒸黏豆包。
开始做饭,我们分工明确:男做菜、女做饭。
表嫂麻利地把淘好的黄米和豆角豆子倒进电饭煲煨煮。两口铁锅,一口撒年糕,一口烙黏面饼子。
撒年糕必须用黄米面,那才是本真的味道。表嫂把那盆干黄米面浇上了温水,用筷子搅了一阵,再用手把疙瘩捏碎。我在盖帘儿上把烀好的豆角豆密密地铺了一层,做年糕,必须用这种豆子才好吃。表嫂均匀地撒上了一层面,待热气上来,面变成了金黄色,我又密密地铺了一层豆子,表嫂又跟着撒了一层面。我是喜欢吃豆子的,于是又铺了浅浅的一层豆,这一锅年糕就撒好了,盖上锅盖,蒸半个小时即可。表妹举着手机,一直在现场直录。
接下来要烙黏面饼子了,依据大家的口味,两种面都烙,馅儿也是两种,红小豆和苏籽。这时的火不能太旺,要文火慢慢烧。我一边添柴,一边瞅着表嫂熟练地揪面、装馅、入锅、拍扁、翻面、起锅,动作迅速而连贯。我告诉表嫂,我要吃最后那个苏籽馅儿的,在锅底多烙一会儿,少放油,烙到外皮酥脆才更好吃。
而另一面的煤气灶旁,表哥变身“大厨”,煎炒烹炸,几样菜很快出锅、装盘。红烧三道鳞、锅包肉、猪肚炒白菜片、肉炒蒜苔、酸菜粉条汤……表姐又弄来几样酱缸里的咸菜。
表嫂喊着:“好饭咯!”一大盘黏面饼,一大盘年糕,一大盘黏米饭陆续端上来。这些古老的“黏货”,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氤氲着土地深远的馈赠和这馈赠后衍生出来的丰收的愉悦。很快,各种饭菜的香气叠加着、融合着,在屋里荡来荡去。我先夹一口黏米饭,蘸点儿苏籽拌糖,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温润而细腻;又夹一口年糕,米香和豆香颤颤地渗透、晃动,好像演绎着岁月静好的动态话本。苏籽馅的黏面饼更让我回味无穷,它把自然美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一种无法言说的艺术美,在我的唇齿间留香,让我的味蕾迸发出无限热情,进而让我感动,不禁脱口而出:“敬天地,敬岁月。”
丰盛的“黏货”饭,在我们的说笑中,在频频举杯中进行着。
吃完饭天还未黑,表弟和表哥去挂灯笼,我们几个表姐妹在表嫂的指挥下开始包黏豆包。先攥豆馅儿,把豆馅儿攥成一个个小圆球,包的时候不散,好包又好看。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包黏豆包让我攥豆馅儿的情景。那昏黄的灯光摇曳着我们的影子,也摇曳着母亲给我讲的一个个关于年的故事与习俗,我一边听一边不时地发问,沉浸在年的神祇和想象里。
人多力量大,两大锅的黏豆包儿很快就包好了,蒸熟,移到高粱秆制作的盖帘上,放到外面冻。零下20多摄氏度豆包很快就冻透了,凿下来,再分装好。我们带着各自的“黏货”告别表哥表嫂返程时,天已经黑透,外面灯笼红彤彤地亮着。
我们穿过许多村庄后,进入了城市的街道。车水马龙,流光溢彩,到处流动着欢快的气息。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念念不忘的是对“黏货”的追寻吗?何止,其实,我们追寻的是对过年意义的探索与延伸,是骨子里对儿时过年的一种留恋与回味,是对大地丰收的一种感恩与分享,更是对美好人世的一种守望。我们带着深情,带着期许,带着祝福,迎接新的自己,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年,就在前头,热气腾腾,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