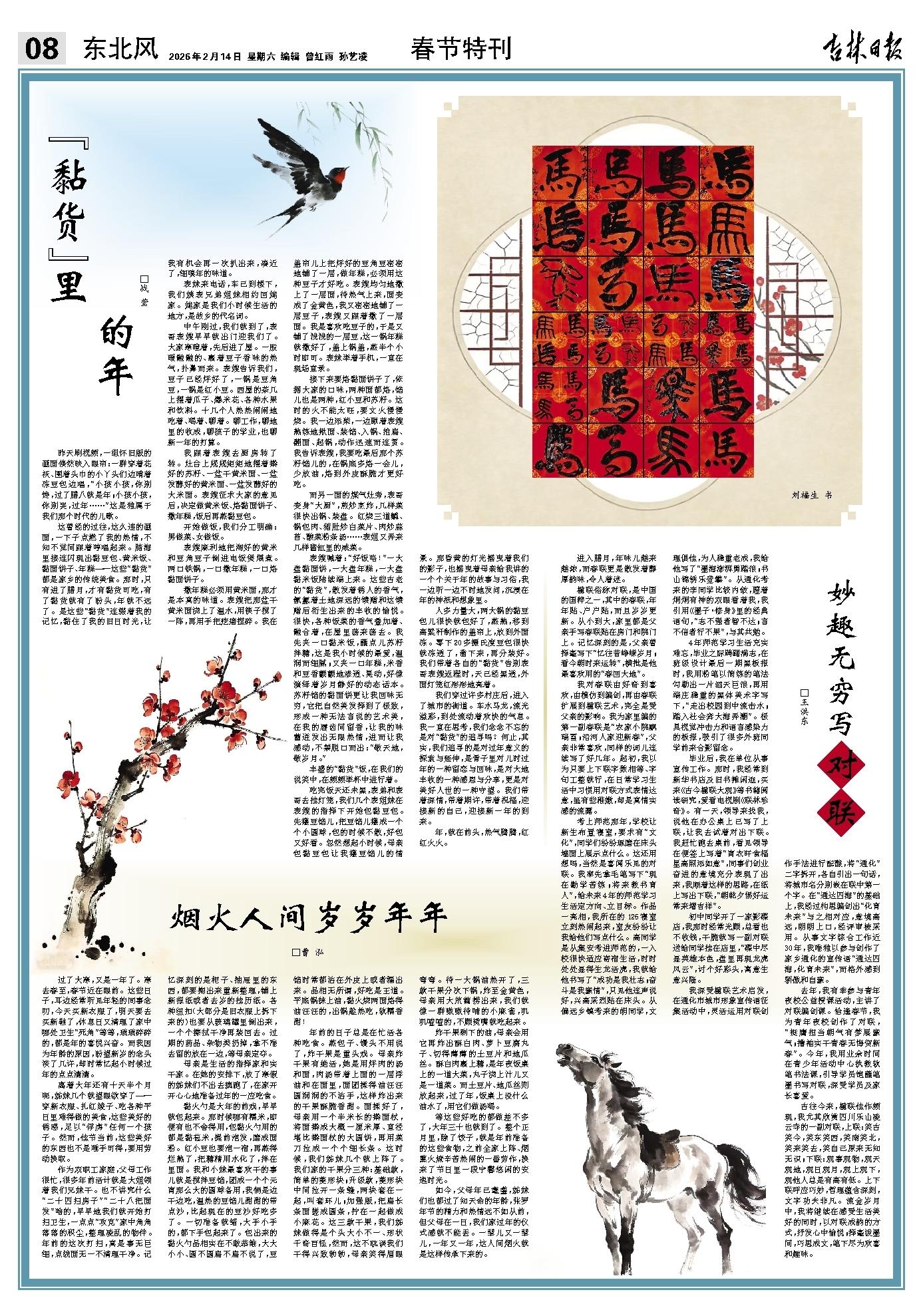过了大寒,又是一年了。寒去春至,春节近在眼前。这些日子,耳边经常听见年轻的同事念叨,今天买新衣服了,明天要去买新鞋了,休息日又清理了家中哪处卫生“死角”等等,琐琐碎碎的,都是年的喜悦兴奋。而我因为年龄的原因,盼望新岁的念头淡了几许,却时常忆起小时候过年的点点滴滴。
离着大年还有十天半个月呢,姊妹几个就望眼欲穿了——穿新衣服、扎红绫子、吃各种平日里难得做的美食,这些美好的诱惑,足以“俘虏”任何一个孩子。然而,佳节当前,这些美好的东西也不是唾手可得,要用劳动换取。
作为双职工家庭,父母工作很忙,很多年前活计就是大姐领着我们兄妹干。也不讲究什么“二十四扫房子”“二十八把面发”啥的,早早地我们就开始打扫卫生,一点点“攻克”家中角角落落的积尘,整理凌乱的物件。年前的这次打扫,真是事无巨细,点线面无一不清理干净。记忆深刻的是柜子、抽屉里的东西,都要掏出来重新整理,铺上新报纸或者去岁的挂历纸。各种纽扣(大部分是旧衣服上拆下来的)也要从玻璃罐里倒出来,一个个擦拭干净再装回去。过期的药品、杂物类扔掉,拿不准去留的放在一边,等母亲定夺。
母亲是生活的指挥家和实干家。在她的安排下,放了寒假的姊妹们不出去疯跑了,在家开开心心地准备过年的一应吃食。
黏火勺是大年的前戏,早早就包起来。那时候哪有糯米,即便有也不舍得用,包黏火勺用的都是黏苞米,提前泡发,磨成面粉。红小豆也要泡一宿,再蒸得烂熟了,把糖精用水化了,拌在里面。我和小妹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搅拌豆馅,团成一个个元宵那么大的圆球备用,我俩是边干边吃,温热的豆馅儿甜甜的带点沙,比起现在的豆沙好吃多了。一切准备就绪,大手小手的,都下手包起来了。包出来的黏火勺品相实在不敢恭维,大大小小、圆不圆扁不扁不说了,豆馅时常都沾在外皮上或者漏出来。品相无所谓,好吃是王道。平底锅抹上油,黏火烧两面烙得油汪汪的,出锅趁热吃,软糯香甜!
年前的日子总是在忙活各种吃食。蒸包子、馒头不用说了,炸干果是重头戏。母亲炸干果有绝活,她是用烀肉的汤和面,肉汤带着上面的一层浮油和在面里,面团揉得油汪汪圆润润的不沾手,这样炸出来的干果酥脆香甜。面揉好了,母亲用一个半米长的擀面杖,将面擀成大概一厘米厚、直径堪比擀面杖的大圆饼,再用菜刀拉成一个个细长条。这时候,我们姊妹几个就上阵了。我们家的干果分三种:基础款,简单的菱形块;升级款,菱形块中间拉开一条缝,两块套在一起,叫套环儿;加强版,把扁长条面搓成圆条,拧在一起做成小麻花。这三款干果,我们姊妹做得是个头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然而,这不耽误我们干得兴致勃勃,母亲笑得眉眼弯弯。待一大锅油热开了,三款干果分次下锅,炸至金黄色,母亲用大笊篱捞出来,我们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麻雀,叽叽喳喳的,不顾烫嘴就吃起来。
炸干果剩下的油,母亲会用它再炸出酥白肉、萝卜豆腐丸子、切得薄薄的土豆片和地瓜丝。酥白肉裹上糖,是年夜饭桌上的一道大菜,丸子浇上汁儿又是一道菜。而土豆片、地瓜丝则放起来,过了年,饭桌上没什么油水了,用它们做汤喝。
等这些好吃的都做差不多了,大年三十也就到了。整个正月里,除了饺子,就是年前准备的这些食物,之前全家上阵、烟熏火燎辛苦热闹的一番劳作,换来了节日里一段宁馨悠闲的安逸时光。
如今,父母年已耄耋,姊妹们也都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张罗年节的精力和热情远不如从前,但父母在一日,我们家过年的仪式感就不能丢。一辈儿又一辈儿,一年又一年,这人间烟火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