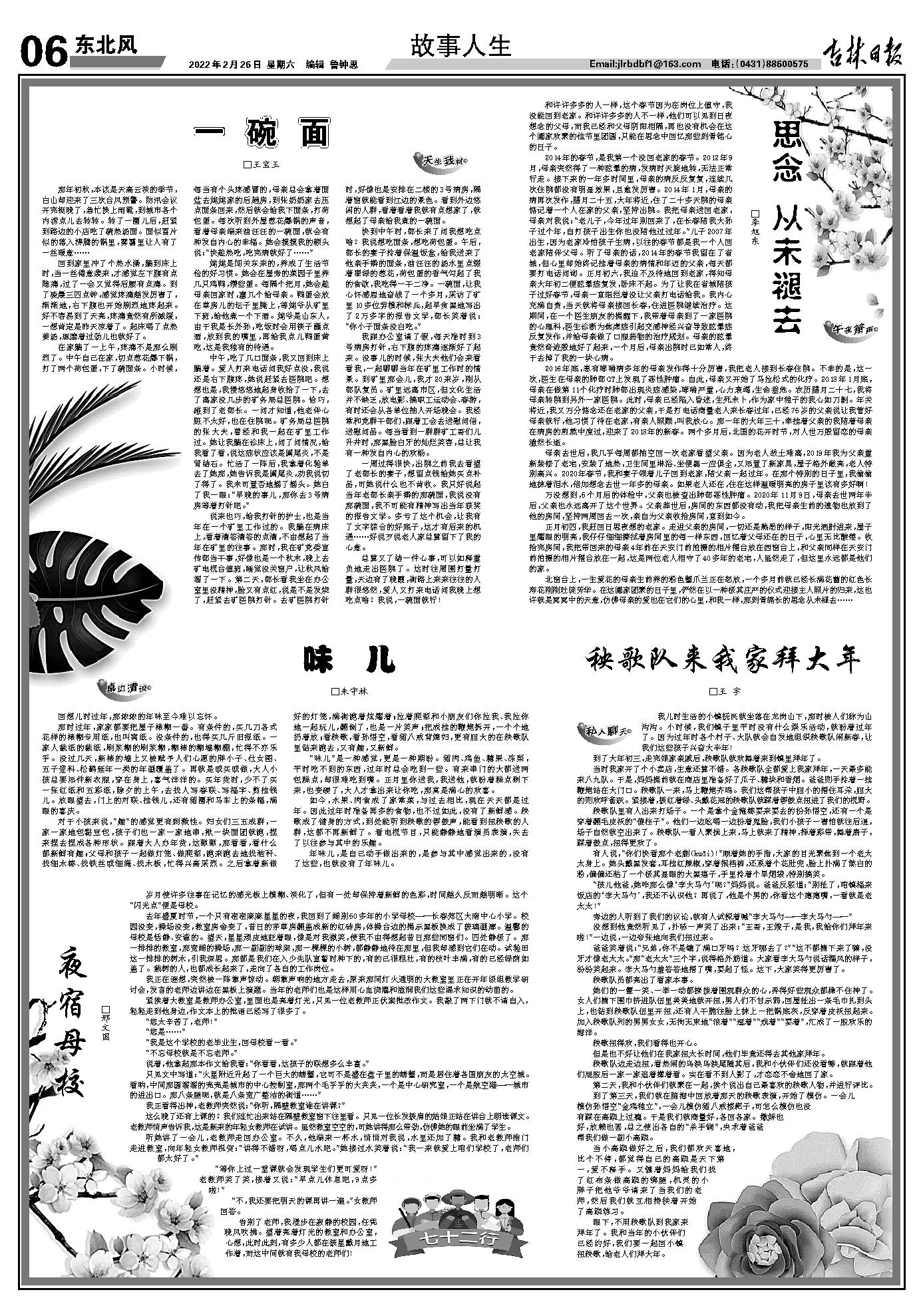我儿时生活的小镇抚民就坐落在龙岗山下,那时被人们称为山沟沟。小时候,我们镇子里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盼着过年了。因为过年时各个村子、大队就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闹新春,让我们这些孩子兴奋大半年!
到了大年初三,走完娘家亲戚后,秧歌队就欢舞着来到镇里拜年了。
当时我家开了个小卖店,生意还算不错。各秧歌队全都爱上我家拜年,一天最多能来八九队。于是,妈妈提前就在商店里准备好了瓜子、糖块和香烟。爸爸则手拎着一挂鞭炮站在大门口。秧歌队一来,马上鞭炮齐鸣。我们这帮孩子中胆小的捂住耳朵,胆大的则欢呼雀跃。紧接着,披红着绿、头戴花冠的秧歌队就踩着锣鼓点扭进了我们的视野。
秧歌队里有人出来打场子。一个是拿个金箍棒耍来耍去的扮孙悟空,还有一个是穿着翻毛皮袄的“傻柱子”。他们一边吆喝一边扮着鬼脸,我们小孩子一害怕就往后退,场子自然就空出来了。秧歌队一看人聚拢上来,马上就来了精神,挥着彩带,舞着扇子,踩着鼓点,扭得更欢了。
有人说,“你们快看那个老蒯(kuǎi)!”顺着她的手指,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一个老太太身上。她头戴黑发套,耳挂红辣椒,穿着抿裆裤,还系着个花肚兜,脸上扑满了煞白的粉,偏偏还粘了一个极其显眼的大黑痦子,手里拎着个旱烟袋,特别搞笑。
“孩儿他爸,她咋那么像‘李大马勺’呢?”妈妈说。爸爸反驳道:“别扯了,咱镇福来饭店的‘李大马勺’,我还不认识他?再说了,他是个男的,你看这个瘪瘪嘴,一看就是老太太!”
旁边的人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就有人试探着喊“李大马勺——李大马勺——”
没想到他竟然听见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王哥,王嫂子,是我,我给你们拜年来啦!”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向我们扭过来。
爸爸笑着说:“兄弟,你不是镶了满口牙吗?这牙哪去了?”“这不都摘下来了嘛,没牙才像老太太。”那“老太太”三个字,说得格外筋道。大家看李大马勺说话漏风的样子,纷纷笑起来。李大马勺羞答答地捂了嘴,耍起了怪。这下,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秧歌队员都亮出了看家本事。
她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撩拨着围观群众的心,弄得好些观众都稳不住神了。女人们摘下围巾挤进队伍里美美地就开扭,男人们不甘示弱,回屋扯出一条毛巾扎到头上,也钻到秧歌队伍里开扭,还有人干脆往脸上抹上一把锅底灰,反穿着皮袄扭起来。加入秧歌队列的男男女女,无拘无束地“浪着”“逗着”“戏着”“耍着”,汇成了一股欢乐的海洋。
秧歌扭得欢,我们看得也开心。
但是也不好让他们在我家扭太长时间,他们毕竟还得去其他家拜年。
秧歌队边走边扭,看热闹的乌泱乌泱尾随其后,我和小伙伴们还没看够,就跟着他们屁股后一家一家追着撵着看。实在看不到人影了,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第二天,我和小伙伴们就聚在一起,挨个说出自己最喜欢的秧歌人物,并进行评比。
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在脑海中回放着那天的秧歌表演,开始了模仿。一会儿模仿孙悟空“金鸡独立”,一会儿模仿猪八戒搂耙子,可怎么模仿也没有踩在高跷上过瘾。于是我们就商量好,各回各家。撒娇也好,放赖也罢,总之使出各自的“杀手锏”,央求着爸爸帮我们做一副小高跷。
当小高跷做好之后,我们都欢天喜地,比个不停,都觉得自己的高跷是天下第一,爱不释手。又缠着妈妈给我们找了红布条做高跷的绑腿,机灵的小胖子把他爷爷请来了当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就互相搀扶着开始了高跷练习。
眼下,不用秧歌队到我家来拜年了。我和当年的小伙伴们已经约好,我们要一起回小镇扭秧歌,给老人们拜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