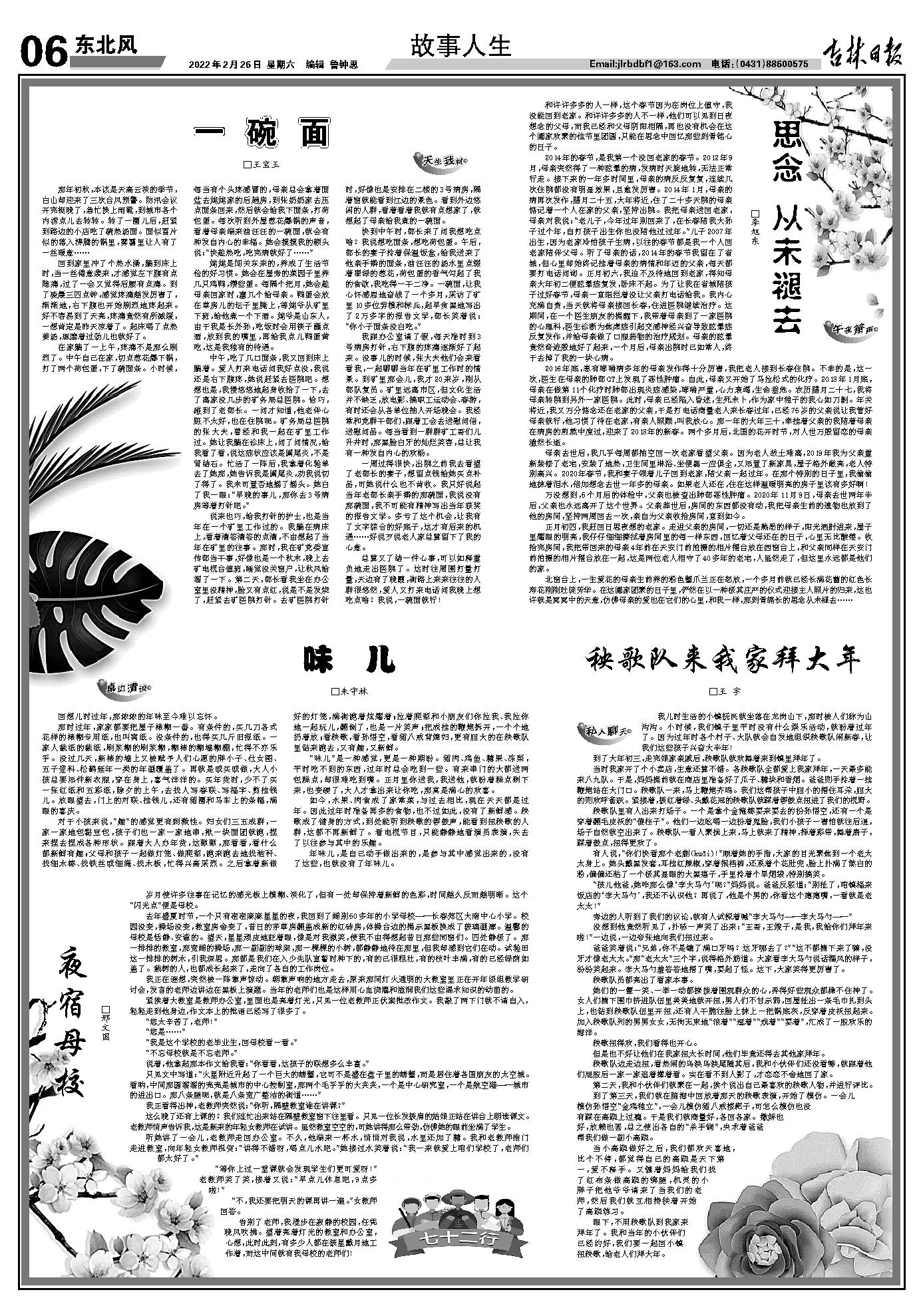回想儿时过年,那浓浓的年味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过年,家家都要把屋子裱糊一番。有条件的,买几刀各式花样的裱糊专用纸,也叫窝纸。没条件的,也得买几斤旧报纸。一家人裁纸的裁纸,刷浆糊的刷浆糊,糊裱的糊墙糊棚,忙得不亦乐乎。没过几天,新裱的墙上又被赋予人们心愿的胖小子、仕女图、五子登科、松鹤延年一类的年画覆盖了。再就是或买或做,大人小孩总要添件新衣服,穿在身上,喜气洋洋的。买年货时,少不了买一张红纸和五彩纸,除夕的上午,去找人写春联、写福字、剪挂钱儿。放眼望去,门上的对联、挂钱儿,还有猪圈和马车上的条幅,满眼的喜庆。
对于小孩来说,“趣”的感觉更有刺激性。妇女们三五成群,一家一家地包黏豆包,孩子们也一家一家地串,揪一块面团就跑,捏来捏去捏成各种形状。跟着大人办年货,这瞅瞅,那看看,看什么都新鲜有趣;父母和孩子一起做灯笼、做爬犁,跑来跑去地找秸秆、找细木棒、找铁丝或细绳、找木板,忙得兴高采烈。之后拿着新做好的灯笼,满街跑着炫耀着;拉着爬犁和小朋友们你拉我、我拉你地一起玩儿,翻倒了,也是一片笑声;把成挂的鞭炮拆开,一个个地扔着放;看秧歌,看孙悟空,看猪八戒背媳妇,更有胆大的在秧歌队里钻来跑去,又有趣,又新鲜。
“味儿”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期盼。猪肉、鸡鱼、糖果、冻梨,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过年时总会吃到一些。有来串门的大都送两包糕点,却很难吃到嘴。正月里你送我,我送他,就盼着糕点剩下来,也变硬了,大人才拿出来让你吃,那真是满心的欢喜。
如今,水果、肉食成了家常菜,与过去相比,现在天天都是过年。因此过年时准备再多的食物,也不过如此,没有了新鲜感。秧歌成了健身的方式,到处能听到秧歌的锣鼓声,能看到扭秧歌的人群,这都不再新鲜了。看电视节目,只能静静地看演员表演,失去了以往参与其中的乐趣。
年味儿,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是参与其中感觉出来的,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年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