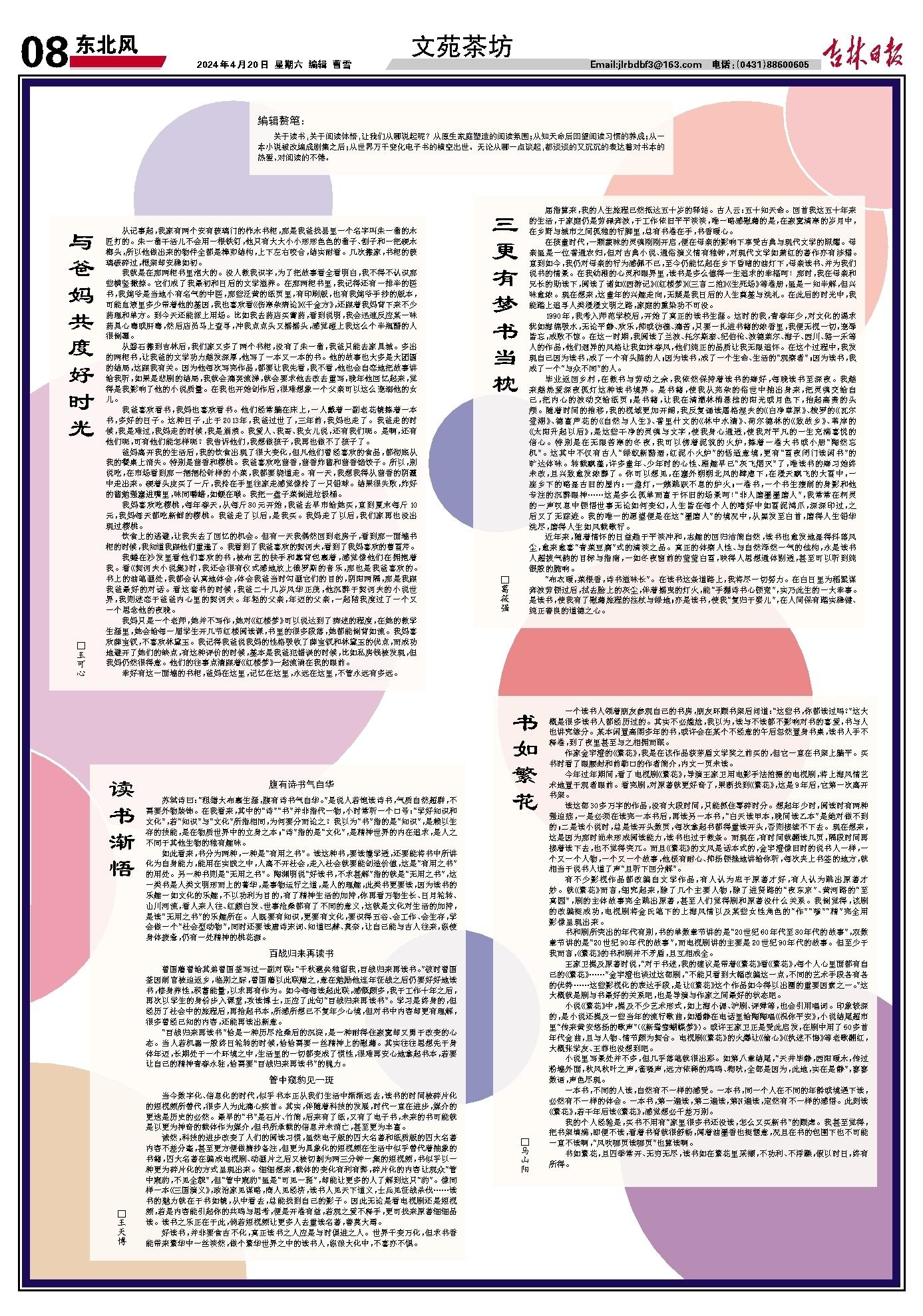一个读书人领着朋友参观自己的书房,朋友环顾书架后问道:“这些书,你都读过吗?”这大概是很多读书人都经历过的。其实不必尴尬,我以为,读与不读都不影响对书的喜爱,书与人也讲究缘分。某本闲置高阁多年的书,或许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忽然置身书桌,读书人手不释卷,到了夜里甚至与之相拥而眠。
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我是在该作品获茅盾文学奖之前买的,但它一直在书架上躺平。买书时看了眼腰封和前勒口的作者简介,内文一页未读。
今年过年期间,看了电视剧《繁花》,导演王家卫用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将上海风情艺术地置于观者眼前。看完剧,对原著就更好奇了,果断找到《繁花》,这是9年后,它第一次离开书架。
读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没有大段时间,只能抓住零碎时分。想起年少时,阅读时有两种强迫症,一是必须在读完一本书后,再读另一本书,“白天读甲本,晚间读乙本”是绝对做不到的;二是读小说时,总是读开头数页,每次拿起书都得重读开头,否则接续不下去。现在想来,这是因为那时尚未形成阅读能力,读书也过于教条。而现在,有时间就翻读几页,隔段时间再接着读下去,也不觉得突兀。而且《繁花》的文风是话本式的,金宇澄像旧时的说书人一样,一个又一个人物,一个又一个故事,他极有耐心、抑扬顿挫地讲给你听,每次夹上书签的地方,就相当于说书人道了声“且听下回分解”。
有不少影视作品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有人认为忠于原著才好,有人认为跳出原著才妙。就《繁花》而言,细究起来,除了几个主要人物,除了进贤路的“夜东京”、黄河路的“至真园”,剧的主体故事完全跳出原著,甚至人们觉得剧和原著没什么关系。我倒觉得,该剧的改编挺成功,电视剧将金氏笔下的上海风情以及某些女性角色的“作”“嗲”“精”完全用影像呈现出来。
书和剧所突出的年代有别,书的单数章节讲的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故事”,双数章节讲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而电视剧讲的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但至少于我而言,《繁花》的书和剧并不矛盾,且互相成全。
王家卫提及原著时说,“对于书迷,我的建议是带着《繁花》看《繁花》,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繁花》……”金宇澄也谈过这部剧,“不能只看到大幅改编这一点,不同的艺术手段各有各的优势……这些影视化的表达手段,是让《繁花》这个作品如今得以出圈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大概就是剧与书最好的关系吧,也是导演与作家之间最好的状态吧。
小说《繁花》中,提及不少艺术形式,如上海小调、沪剧、评弹等,也会引用唱词。印象较深的,是小说还提及一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如潘静在电话里给陶陶唱《祝你平安》,小说结尾超市里“传来黄安悠扬的歌声”(《新鸳鸯蝴蝶梦》)。或许王家卫正是受此启发,在剧中用了50多首年代金曲,且与人物、情节颇为契合。电视剧《繁花》的火爆让《偷心》《执迷不悔》等老歌翻红,大概张学友、王菲也没想到吧。
小说里写景处并不多,但几乎落笔就很出彩。如第八章结尾,“天井毕静,西阳暖木,传过粉墙外面,秋风秋叶之声,雀噪声,远方依稀的鸡鸣、狗吠,全部是因为,此地,实在是静”,寥寥数语,声色尽现。
一本书,不同的人读,自然有不一样的感受。一本书,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或境遇下读,必然有不一样的体会。一本书,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第N遍读,定然有不一样的感悟。此刻读《繁花》,若干年后读《繁花》,感觉想必千差万别。
我的个人经验是,买书不用有“家里很多书还没读,怎么又买新书”的顾虑。我甚至觉得,把书架填满,即便不读,看着书脊就很舒畅,闻着油墨香也挺惬意,况且在书的包围下也不可能一直不读啊,“风吹哪页读哪页”也算读啊。
书如繁花,且四季常开、无穷无尽,读书如在繁花里采撷,不功利、不浮躁,假以时日,终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