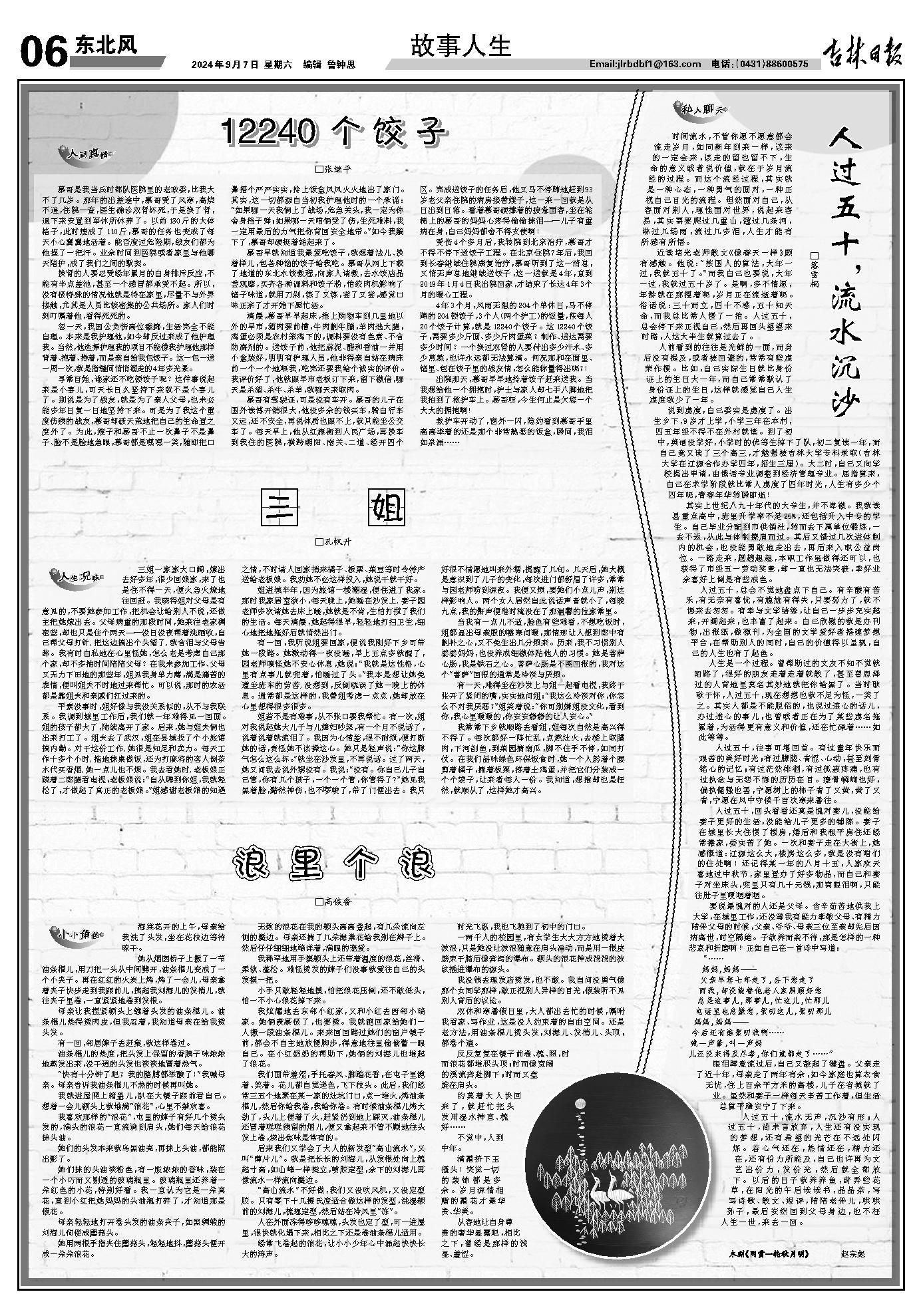海棠花开的上午,母亲给我洗了头发,坐在花枝边等待晾干。
她从烟囱桥子上撅了一节油条棍儿,用刀把一头从中间劈开,油条棍儿变成了一个小夹子。再在红红的火炭上烤,烤了一会儿,母亲拿着夹子快步走到我跟前儿,拽起我刘海儿的发梢儿,就往夹子里卷,一直紧紧地卷到发根。
母亲让我捏紧额头上缠着头发的油条棍儿。油条棍儿热得烫肉皮,但我忍着,我知道母亲在给我烫头发。
有一回,邻居婶子去赶集,就这样卷过。
油条棍儿的热度,把头发上保留的香胰子味浓浓地蒸发出来,没干透的头发也淡淡地冒着热气。
“快有十分钟了吧?我的胳膊都举酸了!”我喊母亲。母亲告诉我油条棍儿不热的时候再叫她。
我就进屋爬上箱盖儿,趴在大镜子跟前看自己。想着一会儿额头上就堆满“浪花”,心里不禁欢喜。
我喜欢那样的“浪花”,屯里的婶子有好几个烫头发的,满头的浪花一直流淌到肩头,她们每天给浪花抹头油。
她们的头发本来就乌黑油亮,再抹上头油,都能照出影了。
她们抹的头油淡粉色,有一股浓浓的香味,装在一个小巧而又剔透的玻璃瓶里。玻璃瓶里还养着一朵红色的小花,特别好看。我一直认为它是一朵真花,直到小红把她妈妈的头油瓶打碎了,才知道那是假花。
母亲轻轻地打开卷头发的油条夹子,如黑绸缎的刘海儿佝偻成蘑菇头。
她用两根手指夹住蘑菇头,轻轻地抖,蘑菇头便开成一朵朵浪花。
无数的浪花在我的额头高高叠起,有几朵流向左侧的鬓边。母亲还摘了几朵海棠花给我别在辫子上。然后仔仔细细地端详着,满眼的宠爱。
我稀罕地用手摸额头上还带着温度的浪花,丝滑、柔软、蓬松。难怪烫发的婶子们没事就爱往自己的头发摸一把。
小手只敢轻轻地摸,怕把浪花压倒,还不敢低头,怕一不小心浪花掉下来。
我炫耀地去东邻小红家,又和小红去西邻小瑞家。她俩羡慕极了,也要烫。我就跑回家给她们一人撅一段油条棍儿。来来回回路过她们的窗户镜子前,都会不自主地放慢脚步,得意地往里偷偷瞥一眼自己。在小红奶奶的帮助下,她俩的刘海儿也堆起了浪花。
我们面带羞涩,手托春风、脚踏花香,在屯子里跑着、笑着。花儿都自觉逊色,飞下枝头。此后,我们经常三五个地聚在某一家的灶坑门口,点一堆火,烤油条棍儿,然后你给我卷,我给你卷。有时候油条棍儿烤大劲了,头儿上便着了火,赶紧扔到地上踩灭,油条棍儿还冒着咝咝残留的烟儿,便又拿起来不管不顾地往头发上卷,烧出焦味是常有的。
后来我们又学会了大人的新发型“高山流水”,又叫“薄片儿”。就是把长长的刘海儿,从发根处向上梳起寸高,如山峰一样挺立,喷胶定型,余下的刘海儿再像流水一样流向鬓边。
“高山流水”不好做,我们又没吹风机,又没定型胶。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适合做这样的发型,洗湿额前的刘海儿,梳理定型,然后站在冷风里“冻”。
人在外面冻得哆哆嗦嗦,头发也定了型,可一进屋里,很快就化塌下来,相比之下还是卷油条棍儿适用。
经常飞卷起的浪花,让小小少年心中涌起快快长大的涛声。
时光飞纵,我也飞驰到了初中的门口。
一两千人的校园里,有女学生大大方方地烫着大波浪,只是她没让波浪随意在肩头涌动,而是用一根皮筋束于脑后像奔泻的瀑布。额头的浪花抻成浅浅的波纹插进瀑布的源头。
我没钱去理发店烫发,也不敢。我自问没勇气像那个女同学那样,敢正视别人异样的目光,假装听不见别人背后的议论。
双休和寒暑假日里,大人都出去忙的时候,嘱咐我看家、写作业,这是没人约束着的自由空间。还是老方法,用油条棍儿烫头发,刘海儿、发梢儿、头顶,都卷个遍。
反反复复在镜子前卷、梳、照,时而浪花都堆积头顶;时而像宽阔的溪流奔赴脚下;时而又盘旋在肩头。
约莫着大人快回来了,就赶忙把头发用湿水抻直、梳好……
不觉中,人到中年。
清霜挤下玉搔头!突觉一切的装饰都是多余。岁月深情相赠的霜花才最华贵、华美。
从容地让自身尊贵的奢华显露吧,相比之下,曾经是那样的浅显、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