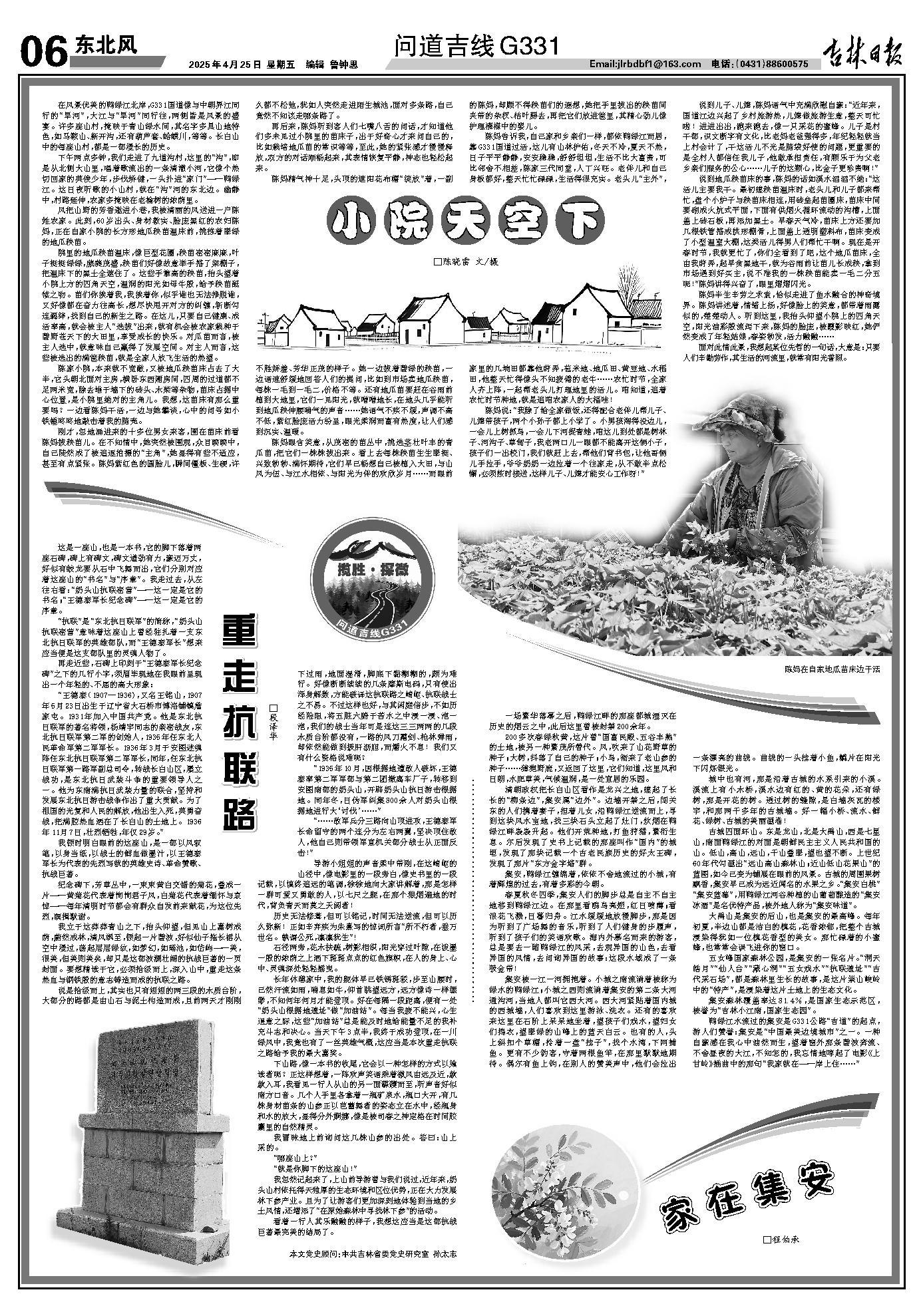这是一座山,也是一本书,它的脚下落着两座石碑,碑上有碑文,碑文遒劲有力,豪迈万丈,好似有蛟龙要从石中飞舞而出,它们分别对应着这座山的“书名”与“序章”。我走过去,从左往右看:“奶头山抗联密营”——这一定是它的书名;“王德泰军长纪念碑”——这一定是它的序章。
“抗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简称,“奶头山抗联密营”意味着这座山上曾经驻扎着一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部队,而“王德泰军长”想来应当便是这支部队里的灵魂人物了。
再走近些,石碑上印刻于“王德泰军长纪念碑”之下的几行小字,须眉毕现地在我眼前呈现出一个年轻的、不屈的高大形象:
“王德泰(1907—1936),又名王铭山,1907年5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詹家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36年3月于安图迷魂阵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同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转战长白山区,屡立战功,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白山的土地上。1936年11月7日,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我顿时明白眼前的这座山,是一部以风驭笔,以身当纸,以战士的鲜血做墨汁,以王德泰军长为代表的先烈写就的英雄史诗、革命赞歌、抗战巨著。
纪念碑下,芳草丛中,一束束黄白交错的菊花,叠成一片——黄菊花代表着恂恂君子风,白菊花代表着缅怀与哀悼——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群众自发前来献花,为这位先烈,瞑揖默谢。
我立于这莽莽青山之下,抬头仰望,但见山上嘉树成荫,蔚然成林,清风飒至,顿起一片碧波,好似仙子拖长裙从空中漫过,荡起层层绿纹,如梦幻,如瑶池,如岱屿——美,很美,但美则美矣,却只是这部波澜壮阔的抗战巨著的一页封面。要想精读于它,必须拾级而上,深入山中,重走这条热血与钢铁般的意志铸造而成的抗联之路。
说是拾级而上,其实也只有短短的两三段的木质台阶,大部分的路都是由山石与泥土构造而成,且前两天才刚刚下过雨,地面湿滑,脚底下黏糊糊的,颇为难行。好像断断续续的几条摩斯电码,只有使出浑身解数,方能破译这抗联路之崎岖、抗联战士之不易。不过这样也好,与其闲庭信步,不如历经险阻,将五脏六腑于苦水之中浸一浸、泡一泡,我们的战士当年可是连这三三两两的几段木质台阶都没有,一路的风刀霜剑、枪林弹雨,却依然能做到披肝沥胆,而爝火不息!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难呢?
“1935年10月,因根据地遭敌人破坏,王德泰率第二军军部与第二团撤离车厂子,转移到安图南部的奶头山,开辟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冬,日伪军纠集800余人对奶头山根据地进行大‘讨伐’……”
“……敌军兵分三路向山顶进攻,王德泰军长命留守的两个连分为左右两翼,坚决顶住敌人,他自己则带领军直机关部分战士从正面反击!”
导游小姐姐的声音柔中带刚,在这崎岖的山径中,像电影里的一段旁白,像史书里的一段记载,以慎终追远的笔调,徐徐地向大家讲解着,那是怎样一群可爱又勇敢的人,以七尺之躯,在那个狼烟遍地的时代,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
历史无法修葺,但可以铭记,时间无法逆流,但可以历久弥新!正如辛弃疾为朱熹写的悼词所言“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石径两旁,花木扶疏,树影相织,阳光穿过叶隙,在泼墨一般的浓荫之上洒下斑斑点点的红色旗帜,在人的身上、心中、灵魂深处轻轻摇曳。
长年休憩家中,我的躯体早已铁锈斑驳,步至山腰时,已然汗流如雨,喘息如牛,仰首眺望远方,远方像诗一样缥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登顶。好在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处“奶头山根据地遗址”做“加油站”。每当我疲不能兴,心生退意之际,这些“加油站”总是能及时地给能量不足的我补充斗志和决心。当天下午3点半,我终于成功登顶,在一川绿风中,我竟也有了一丝英雄气概,这应当是本次重走抗联之路给予我的最大嘉奖。
下山路,像一本书的收尾,它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以飨读者呢?正这样想着,一阵欢声笑语乘着微风由远及近,款款入耳,我看见一行人从山的另一面蹀躞而至,听声音好似南方口音。几个人手里各拿着一瓶矿泉水,瓶口大开,有几株身材苗条的山参正以芭蕾舞者的姿态立在水中,经瓶身和水的放大,显得分外婀娜,像是被司春之神定格在时间胶囊里的自然精灵。
我冒昧地上前询问这几株山参的出处。答曰:山上采的。
“哪座山上?”
“就是你脚下的这座山!”
我忽然记起来了,上山前导游曾与我们说过,近年来,奶头山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正在大力发展林下参产业。且为了让游客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当地的乡土风情,还增添了“在原始森林中寻找林下参”的活动。
看着一行人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想这应当是这部抗战巨著最完美的结局了。
本文党史顾问: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孙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