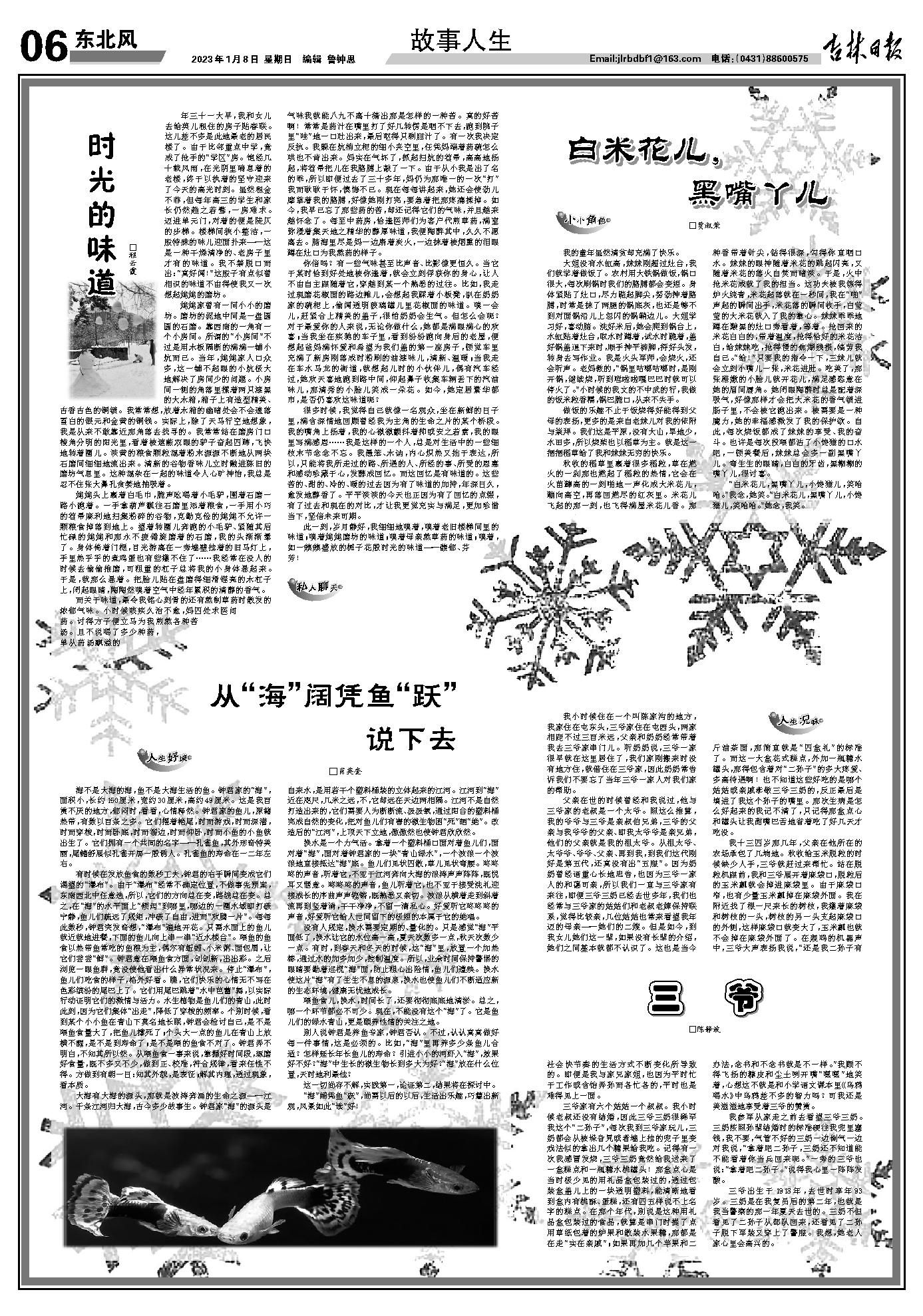我的童年虽然清贫却充满了快乐。
大姐没有水缸高,妹妹刚超过灶台,我们就学着做饭了。农村用大铁锅做饭,锅口很大,每次刷锅时我们的胳膊都会变短。身体紧贴了灶口,尽力踮起脚尖,努劲抻着胳膊,时常是抹了两腿的锅底灰,也还是够不到对面锅沿儿上忽闪的锅鞘边儿。大姐学习好,喜动脑。洗好米后,她会爬到锅台上,水缸贴着灶台,取水时蹲着,试水时跪着,盖好锅盖退下来时,顺手抻平裤脚,捋好头发,转身去写作业。我是火头军师,会烧火,还会听声。老妈教的,“锅里咕嘟咕嘟时,是刚开锅,继续烧,听到咝啦啦嘎巴巴时就可以停火了。”小时候的我文的不中武的行,我做的饭米粒香糯,锅巴脆口,从来不失手。
做饭的乐趣不止于饭烧得好能得到父母的表扬,更多的是来自老妹儿对我的依附与崇拜。我们这是平原,没有大山,旱地少,水田多,所以烧柴也以稻草为主。就是这一捆捆稻草给了我和妹妹无穷的快乐。
秋收的稻草里裹着很多稻粒,草在燃火的一刹那也燃起了稻粒的热情,它会在火苗蹿高的一刻啪地一声化成大米花儿,蹦向高空,再落回燃尽的红灰里。米花儿飞起的那一刻,也飞得满屋米花儿香。那种香带着针尖,钻得很深,勾得你直咽口水。妹妹的眼神随着米花的跳起闪亮,又随着米花的落火自焚而暗淡。于是,火中抢米花成就了我的担当。这功夫被我练得炉火纯青,米花起落就在一秒间,我在“啪”声起的瞬间出手,米花落的瞬间收手,白莹莹的大米花就入了我的掌心。妹妹乖乖地蹲在黢黑的灶口旁看着,等着。抢回来的米花白白的,带着温度,抢得恰好的米花洁白,给妹妹吃,抢得慢的焦煳残损,犒劳我自己。“给!”只要我的指令一下,三妹儿就会立刻小嘴儿一张,米花进肚。吃美了,那张稚嫩的小脸儿就开花儿,满足感恣意在她的眉间唇角。她闭眼陶醉时总是配着深吸气,好像那样才会把大米花的香气锁进肠子里,不会被它跑出来。被需要是一种魔力,她的幸福感激发了我的保护欲。自此,每次烧饭都成了妹妹的享受、我的奋斗。也许是每次投喂都沾了小馋猫的口水吧,一顿美餐后,妹妹总会多一副黑嘴丫儿。弯生生的眼睛,白白的牙齿,黑糊糊的嘴丫儿,很讨喜。
“白米花儿,黑嘴丫儿,小馋猫儿,笑哈哈。”我念,她笑。“白米花儿,黑嘴丫儿,小馋猫儿,笑哈哈。”她念,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