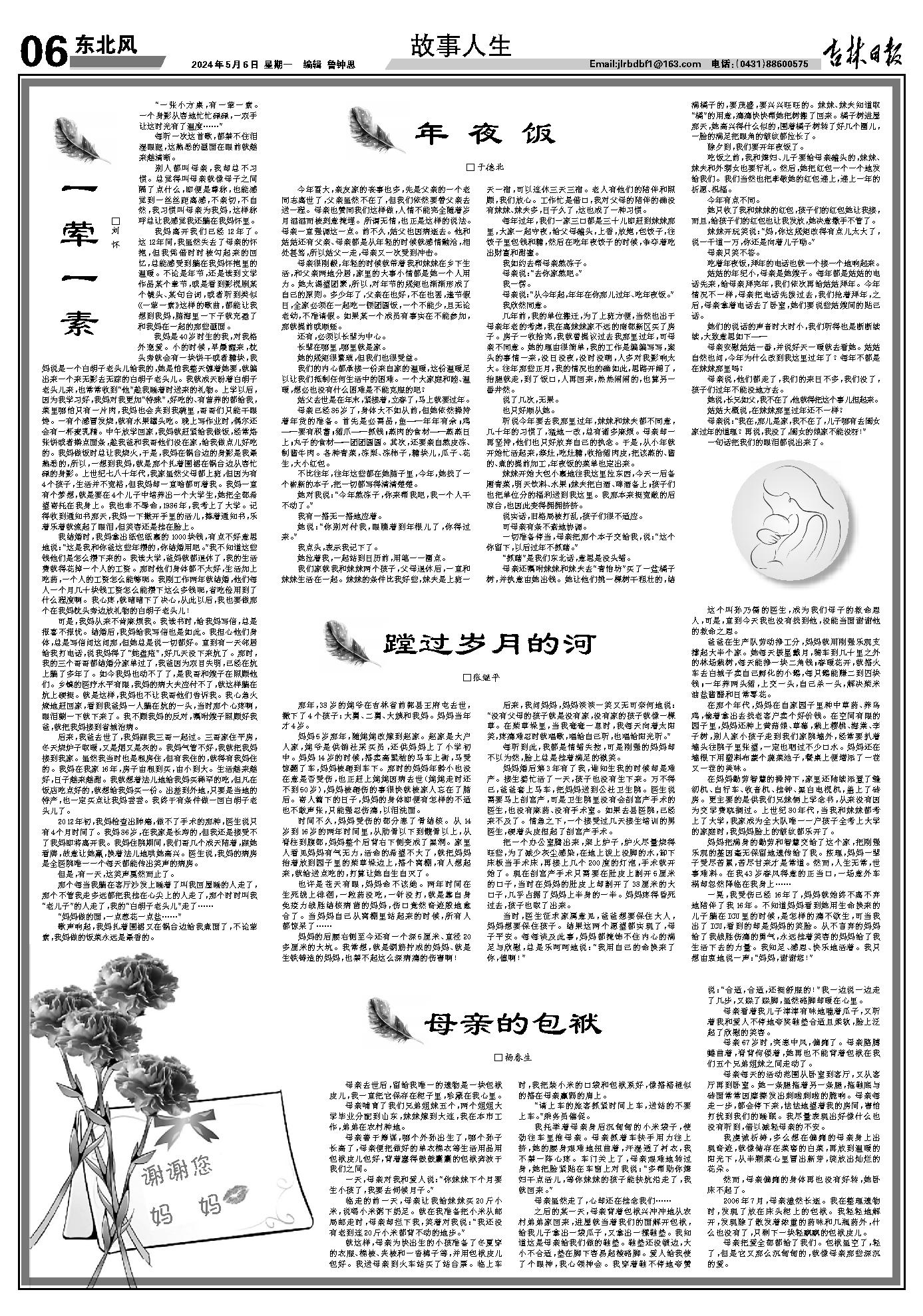今年雪大,亲友家的丧事也多,先是父亲的一个老同志离世了,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我们依然要替父亲去送一程。母亲也赞同我们这样做,人情不能完全随着岁月滔滔而被刻意掩埋。所谓无情,也正是这样的说法。母亲一直强调这一点。前不久,姑父也因病逝去。他和姑姑还有父亲、母亲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感情融洽,相处甚笃,所以姑父一走,母亲又一次受到冲击。
母亲很刚毅,年轻的时候就带着我和妹妹在乡下生活,和父亲两地分居,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一个人用力。她太渴望团聚,所以,对年节的规矩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原则。多少年了,父亲在也好,不在也罢,逢节假日,全家必须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一个不能少,且无论老幼,不准请假。如果某一个成员有事实在不能参加,那就提前或顺延。
还有,必须以长辈为中心。
长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她的规矩很繁琐,但我们也很受益。
我们的内心都承接一份来自家的温暖,这份温暖足以让我们抵制任何生活中的困难。一个大家庭和睦、温暖,想必也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吧?
姑父去世是在年末,紧接着,立春了,马上就要过年。
母亲已经85岁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但她依然操持着年货的准备。首先是必需品,鱼——年年有余;鸡——要有积蓄;猪爪——抓钱;蒸肉的食材——蒸蒸日上;丸子的食材——团团圆圆。其次,还要亲自熬皮冻、制酱牛肉。各种青菜,冻梨、冻柿子,糖块儿,瓜子、花生,大小红包。
不比往年,往年这些都在她脑子里,今年,她找了一个崭新的本子,把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
她对我说:“今年熬冻子,你来帮我吧,我一个人干不动了。”
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应着。
她说:“你别对付我,眼瞧着到年根儿了,你得过来。”
我点头,表示我记下了。
她拉着我,一起站到日历前,用笔一一圈点。
我们家就我和妹妹两个孩子,父母退休后,一直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妹妹的条件比我好些,妹夫是上班一天一宿,可以连休三天三宿。老人有他们的陪伴和照顾,我们放心。工作忙是借口,我对父母的陪伴的确没有妹妹、妹夫多,日子久了,这也成了一种习惯。
每年过年,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三十儿即赶到妹妹那里,大家一起守夜,给父母磕头,上香,放炮,包饺子,往饺子里包钱和糖,然后在吃年夜饺子的时候,争夺着吃出财富和甜蜜。
我如约去帮母亲熬冻子。
母亲说:“去你家熬吧。”
我一愣。
母亲说:“从今年起,年年在你那儿过年、吃年夜饭。”
我欣然同意。
几年前,我的单位搬迁,为了上班方便,当然也出于母亲年老的考虑,我在离妹妹家不远的南部新区买了房子。房子一收拾完,我就曾提议过去我那里过年,可母亲不同意。她的理由很简单,我的工作是编编写写,案头的事情一来,没日没夜,没时没晌,人多对我影响太大。往年那些正月,我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思路开阔了,抬腿就走,到了饭口,人再回来,热热闹闹的,也算另一番井然。
说了几次,无果。
也只好顺从她。
听说今年要去我那里过年,妹妹和妹夫都不同意,几十年的习惯了,猛地一改,总有诸多麻烦。母亲却一再坚持,他们也只好放弃自己的执念。于是,从小年就开始忙活起来,祭灶,吃灶糖,收拾猪肉皮,把该蒸的、酱的、煮的提前加工,年夜饭的菜单也定出来。
妹妹开始大包小裹地往我这里拉东西,今天一后备厢青菜,明天饮料、水果;妹夫把白酒、啤酒备上;孩子们也把单位分的福利送到我这里。我那本来挺宽敞的后凉台,也因此变得拥拥挤挤。
说实话,旧格局被打乱,孩子们很不适应。
可母亲有条不紊地协调。
一切准备停当,母亲把那个本子交给我,说:“这个你留下,以后过年不抓瞎。”
“抓瞎”是我们东北话,意思是没头绪。
母亲还嘱咐妹妹和妹夫去“青怡坊”买了一盆橘子树,并执意由她出钱。她让他们挑一棵树干粗壮的,结满橘子的,要茂盛,要兴兴旺旺的。妹妹、妹夫知道取“橘”的用意,痛痛快快帮她把树搬了回来。橘子树进屋那天,她高兴得什么似的,围着橘子树转了好几个圈儿,一脸的满足把眼角的皱纹都拉长了。
除夕到,我们要开年夜饭了。
吃饭之前,我和媳妇、儿子要给母亲磕头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也要行礼。然后,她把红包一个一个地发给我们。我们当然也把孝敬她的红包递上,递上一年的祈愿、祝福。
今年有点不同。
她只收了我和妹妹的红包,孩子们的红包她让我接,而且,给孩子们的红包也让我发放,她决意撒手不管了。
妹妹开玩笑说:“妈,你这规矩改得有点儿太大了,说一千道一万,你还是向着儿子呦。”
母亲只笑不答。
吃着年夜饭,拜年的电话也就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
姑姑的年纪小,母亲是她嫂子。每年都是姑姑的电话先来,给母亲拜完年,我们依次再给姑姑拜年。今年情况不一样,母亲把电话先拨过去,我们抢着拜年,之后,母亲拿着电话去了卧室,她们要说些姑嫂间的贴己话。
她们的说话的声音时大时小,我们听得也是断断续续,大致意思如下——
母亲安慰姑姑一番,并说好天一暖就去看她。姑姑自然也问,今年为什么改到我这里过年了?每年不都是在妹妹那里吗?
母亲说,他们都走了,我们的来日不多,我们没了,孩子们过年不能没地方去。
她说,长兄如父,我不在了,他就得把这个事儿担起来。
姑姑大概说,在妹妹那里过年还不一样?
母亲说:“我在,那儿是家,我不在了,儿子哪有去闺女家过年的道理?再说,我没了,闺女的娘家不能没呀!”
一句话把我们的眼泪都说出来了。